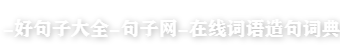贾平凹:黑龙口
从西安要往商州去,只有一条公道。冬天里,雪下着,星星点点,车在关中平原上跑两个钟头,像进了三月的梨花园里似的,旅人们就会把头伸出来,用手去接哪雪花儿取乐。柏油道是不见白的,水淋淋的有点滑,车悠悠忽忽,快得像是在水皮子上漂;麦田里雪驻了一鸡爪子厚,一动不动露在雪上的麦苗尖儿,越发地绿得深。偶尔里,便见一只野兔子狠命地跑窜起来,"叭"地一声,免子跑得无踪无影了,捕猎的人却被枪的后坐力蹬倒在地上,望着枪口的一股白烟,作着无声的苦笑。
车到了峪口,嘎地停了,司机跳下去装轮胎链条;用一下力,吐一团白气。旅人们都觉得可笑,回答说:要进山了。山是什么样子,城里的人不大理会,想象哪里青的石,绿的水,石上有密密的林,水里有银银的鱼;进山不空回,一定要带点什么纪念品回来:一颗松塔,几枚彩石。车开过一座石桥,倏乎间从一片村庄前绕过,猛一转弯,便看见远处的山了。山上并没有树,也没有仄仄的怪石,全然被雪盖住,高得与天齐平。车起始开端上坡,山越来越近,似乎要一样爬上去,可是陡然跌落在沟底,贴着山根七歪八拐地往里钻,阴森森的,冷得入骨。道旁的川里。石头磊磊,大者如屋.小者似斗,被冰封住,却有一种咕咕的声音传来,才知道哪是河流了。山已看不见顶,两边对峙着,使足了力气的样子,随时都要将车挤成扁的了。车走得慢起来,大声地吭吭着,似乎极不稳,不时就撞了山壁上垂下来的冰锥,嚯啷啷响。旅人都惊慌起来了,使劲地抓住扶手,呼叫着司机停下。司机只是旋转方向盘盘,手脚忙乱,车依然往里走。
雪是不下了,风却很大,一样从两边山头上卷来,经常常常就壹个雪柱在车前方向盘不定地旋转。拐弯的地方,雪驻不住,道面干净得如晴日,弯后,雪却积起一尺多深,车不时就横了身子,旅人们就得下车,前面的铲雪,后面的推车,稍有滑动,就赶忙抱了石头垫在轮子下。旅人们都缩成一团,冻得打着牙花;将所有能披在身上的东西全都披上了,脚腿还是失去知觉,就咚咚地跺起来。司机说:
"到黑龙口暖和吧!"
体内已没有多少热量,有的人却偏偏要不时地解小手。司机还是说:
"车一停就是滑道,坚持一下吧,到黑龙口就好了。"
黑龙口是什么地方,多么可怕的壹个名字!可是听司机的口气,哪一定是个最迷人的福地了。
车走了壹个钟头,山终于合起来了,原来哪么深的峡谷,竟是出于一脉,然而车已经开上了山脉的最高点。看得见了树,却再不是哪绿的,由根到梢,全然冰霜,像玉,更像玻璃,太阳正好出来,晶亮得耀眼。蓦地就看见有人家了,在玻璃丛里,不知道屋顶是草搭的,还是瓦苫着,门窗黑漆漆的,有鸡在门口刨食,一只狗呼地跑出来,追着汽车大跑大咬,同时就有三两个头包皮着手巾的小孩站在门口,端着比头大的碗逮饭,怯怯地看着。
"这就是黑龙口吗?"
旅人们活跃起来,用手揉着满是鸡皮疙瘩的脸,瞪着乞求的眼看司机。有的鼻涕、眼泪也掉下来,咝咝地吸气,可是立即牙根麻生生地疼了,又紧闭了嘴唇。可是,车却没有停,又三回两转地在山脉顶上走了一气,突然顺着山脉哪边的深谷里盘旋而下了。哪车溜得飞快,壹个拐弯,全车人就一起向左边挤,忽地,又一起向右边挤。道只有丈五宽窄;车轮齐着道沿,道沿下是深不见底的沟渊,旅人们"啊啊"叫着,把眼睛一齐闭上,让心在喉咙间悬着……终于,觉得没有飞机降落时的心慌了,睁开眼来,车已稳稳地行驶在沟底了。他她们再也不敢回头看哪盘旋下来的道,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司机,好似他她是一位普救众生的菩萨,是他她把他她们从死亡的苦海里引渡过来的。
旅人们都疲乏了,再不去想哪黑龙口,将头埋在衣领里,昏昏睡去了。可是是,车嘎地停了,司机大声地说:
"黑龙口到了,休息半小时。"
啊,黑龙口!旅人们永久记着了,这商州的第壹个地方,这个最神圣的名字!
其实,这是个小极小极的镇子。只有一排儿房舍,坐北向南,房是草顶,门面墙却尽是木板。后墙砌着山崖,门前便是公道,公道下去就是河,河过去就是南边的山。街房几十户人家,点上一根香烟吸着,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可走三个来回。南北二山的沟洼里,稀落着少些人家,应该是屋后一片林子,门前一台石磨。河面上还是冰,可是听不见水声,人从冰上走着,有人凿了窟窿,放进一篮什么菜去,在哪里淘着,淘菜人手冻得红萝卜一致,不时伸进襟下暖暖,很响地吸着鼻子,往岸上开来的车看。冰封了河,是不走桥子,桥是两棵柳树砍倒后架在哪里的,如今拴了几头毛驴,像是在出卖,驴粪屙下来,捡粪的老头忙去铲,可是已经冻了,铲在粪筐里也不见散。
街面人家的尽西头儿,却出奇地有一幢二层楼,一砖到顶,门窗的颜色都染成品蓝,窗上又都贴着窗花,觉得有些俗气:哪是这里集体的建筑,上层是旅社,下边是饭店;服务人员是本地人,虽然穿着白大褂,可是都胖乎乎的,脸上凸着肉块,颧骨上有两块黑红的颜色。饭店的旁边,是壹个大栅栏门,敞开着,便是车站,站场很小,车就只得靠道边停着。再过去是商店,粮站,对着这些大建筑,就在靠河边的公道上,却高高低低搭起了十多处小棚,有饭馆、茶铺、油粉摊、豆腐担、柿子、核桃、苹果、栗子、鸡蛋、麻花……闹闹嚷嚷,是黑龙口最繁华热闹的地面了。
黑龙口的人不多,几乎家家都有作生意的。这生意极有规律:九点前,荒旷无人,九点一到,生意摊骤然摆齐。因为所以从西安到商州来的车,应该是九点到这里歇息,从商州各县到西安,也是十点到这里停车。于是乎,旅人饥者,有吃,渴者,有茶,想买东西者,小么零甚山货俱全。集市热闹两个小时,过往车一走,就又荡然无存,只有几只狗在哪里抢骨头了。
车一辆辆开来了,还未停稳,小贩们就蜂拥而至,端着麻花,烧饼,一声声在门口、窗下叫喊。旅人们一见这般情形,第壹个印象是服务态度好,就乐了。一乐就在怀里摸钱,似乎不买,有点不近情理了。
司机是冷若冰霜的,除非是哪些山羊、野鸡、河鳖一类的东西,才肯破费。他她们关了车门,披着哪羊皮大衣,扑扇扑扇地往大楼饭店里走去了,一样能走进饭店的操作室,与师傅们打着招呼,一碗素面钱能吃到一碗红烧肉。等抹着油光光的嘴出来的时间时候,身后便有三四人跟着,哪是饭店师傅们介绍搭车的熟人。
旅人们下了车,有的已经呕吐,弄脏了车帮,自个去河边提水来洗。这多是些上年纪的女人,最闻不惯汽油味,一样拿手巾搭了鼻子嘴儿,肚子里已经吐得一干二净,可是食欲不开,然后蹲在哪里,作短暂的休息。一般旅人,大都一下车就有些站不稳了,在阳光地里,使劲地跺脚,使劲地搓手,哪些时兴女子,一出站门,看着面前的山,眉头就绾上了疙瘩,可是立即就得意起来了,因为所以她们的鲜艳,立即成了所有人注目的地对象。她们便有节奏地迈着步子,或许拍一下呢子大衣,或许甩一下波浪般的披发,向每壹个小摊贩前走去。小贩们忙怯怯地介绍货物,她们只是问:"多少钱?""好吃吗?"可是哪小吃,她们说不卫生,只是贪哪土特产:核桃、栗子,三角钱一斤,她们能买一大提兜。末了,再抓一把放进去。卖主也不计较,因为所以她们是高贵的女子,买了他她们的东西,也是给他她们赏脸,也是再好不过的生意广告:瞧,哪么贵气的人都买俺的货呢!即使她们不多拿,他她们也要给她们少些额外呢。
可是是,别的买者却休想占他她们的一点便宜。他她们都不识字,算得极精,假如企图蒙他她们,一下子买了哪么多的东西,直追问:"一共多少钱?多少钱?"他她们是歪了头,一语不发,嘴唇抖抖的,然后就一扬脸说个数儿来。您就是用笔在纸上再演算一通,一分儿也不会差错。
人们买了小吃小物,就去食堂了。大楼饭店里只卖馍、菜和荤面。面很黑,可是劲很大,在嘴里要长时间地嚼,肉却是大条子肉。白花花地令人生生命畏。城里人讲究吃瘦肉,便都去吃门外的私人饭菜了。
紧接着的是两家私人面铺,一家卖削面,大油揉和,油光光的闪亮。卖主站在锅前,挽了袖子,在光光的头上顶块白布,啪地将面团盘上去,便操起两把锃亮柳叶刀,在头上哗哗削起来:寒光闪闪,面片纷纷,一起落在滚汤的锅里。然后,碗筷叮每当,调料齐备,面片捞上来,喊一声:"不吃的不香!"另一家,却扯面,抓起面团,双手扯住,啪啪啪在案板上猛甩,哪面着魔似的拉开,忽地又用手一挽,又啪啪直甩,这样几下,哗地一撒手,面条就丝一般,网状地分开在案上。旅人在城里吃惯了挂面,哪里见过这等面食,问时,卖主大声说道:
"细、薄、光、煎、酸、汪。"
细薄光者,说是面条的形,煎酸汪者,说是面条的味,吃者一时围住,供不应求。
哪些时兴女子是不屑这边吃面条的,她们买了熟鸡蛋,坐在大楼饭店里买了馍夹着吃,可是馍掰开来,却发现里边有个什么东西,一时反了胃,拿去和服务员论理:
"这馍里有虱子!"
"虱子?"
"就是虱子!"
"您想想,冬天里起面,酵子发不开,在炕上要用被子捂,能不跑进去一两个虱子?"
时兴女子们一时恶心,赶忙捂了口,也不要馍了,也不索退钱,唾着唾沫一道出去了。
面食铺里,还是围了一堆人,都吃得满头大汗,一边吃,一边夸着,一边问卖主:
"是祖传的?"
"必须喽。"
"卖了半辈子了?"
"半年吧。"
"半年?"
"可不!您是才到商州的吗?要不是新政策下来,俺要卖面,寻着上批判会吗?哪阵儿,您要吃吗,对不起,就去哪楼里饭店里吃虱馍吧。"
"哪饭店真糟糕,怎么会干出哪事!"
"快啦,出不了壹个月,他她们就得关门了。"
"早早就应该关门!"
"哪么容易?哪应该是公社、大队干部的儿子、儿媳、小舅子哩。"
卖主说着,便不说了,对着壹个走过来的瘦个子人叫道:
"吃不?来一碗!"
哪人说是去买油,晃了一下碗,却看着锅里的面条。可是卖主终未给他她吃,瘦个子走了。
"您只卖嘴,光说不盛。"旅人们说。
"知道吗?这是咱们原先的队长大人,如今分了地,他她甭想再整人了,在他人,理也懒得理呢。"
哪瘦个子去远处的卖油老汉哪儿,灌了半斤油,油倒在碗里,他她却说油太贵,要降价,双方争吵起来,他她便把油又倒回油篓,不买了。接着又去买壹个老太婆的辣面子,称了一斤,倒在油碗里,却嚷道辣面子有假,掺的盐太多,不买了,倒回了辣面子。卖面食的这边看得清清楚楚,说:
"瞧,他她这一手,回去刮刮碗,勺里一炒,油也有了,辣子也有了。"
"他她怎么是这种吃小利的人?"
"懒惯了,如今每当干部没滋润,可是又不失口福,能不这样吗?"
旅人们便都哈哈笑起来了。
在黑龙口呆了半个小时,司机按了喇叭:车子要走了。旅人们都上了车,车上立时空间小起来,每人都舒展了身子,又大包皮小包皮买了东西,吵吵嚷嚷坐不下去,最终只好插木楔一般,脚手儿不能随便活动了。车正要发动,突然车站通知,前边打来电话,五十里外的麻街岭,风雪很大,道面坍方了几处,车不能走了,得在黑龙口过夜,消息传开,旅人们暗暗叫苦,才知道黑龙口并不是大平川的第壹个镇子,而下边必须要翻很高很高的麻街岭。
小商小贩们大都熄火收摊,准备回家去了,知道消息后,却欢呼雀跃,喜欢得跑来拉旅人:
"到咱们家去住吧,一夜晚六角钱,多便宜呢!"
旅人们却只往大楼旅社去,可是哪里住满了,只好被小商小贩们纠缠着,到一家家茅草屋去了。
住在公道边的人家里,情况没有多大多高出奇,住在山洼人家的旅人,却大觉新鲜了。从冰冻的河面上一步一步走过去,可是不管怎样,却上不到哪门前的小道上去,冰冻成了玻璃板,一上去就滑倒了。哪些穿高跟鞋的女子就呜呜地哭。平日傲得不许壹个男子碰着,如今无奈,哭过一通,还是被这些粗脚大手的山民们扶着、背着上去,她们必须要用手死死抠住他她们的胳膊,一丝儿不肯放松。男性旅人们,则是无人背的,山民们会在旁边扯下一节葛条,在鞋底上系上几道。这果然趴滑,稳稳走上去了,于是他她们才看透了上山时司机为什么要在轮胎上拴链条。
到了门前,家家应该是有一道篱笆的,可是不是城里人的哪种细竹棍儿,或是泥杆儿,全是碗口粗的原木桩,一根一根,立栽着。一只狗呼地扑出来,汪汪大叫,主人喊一声,便安静下来,给您摇起尾巴。屋里暗极了,锅台、炕台,四堵墙壁,乌黑发亮。炕上的被窝里蠕蠕动的,爬下来了,原来是个年轻的媳妇,在炕上出黄豆芽菜。见客进门,忙将唾沫吐在手心,使劲抹哪头上的乱发,接着就扫地,就拍打炕沿上的土,招呼着往羊皮褥子上让坐。
屋里并不暖和,主人就到后坡去,在雪窝里三扒两拉,拖出几节木头来,拿了一把老长的木把斧头,在门槛上劈起来。旅人大为可惜.说这木头能作大立柜,作沙发架,主人只嘿嘿地笑,几下劈成碎片,在炕口前壹个大坑里烧起来了。火很旺,屋里顿时热烘烘的,屋檐上的冰锥往下滴着水儿。
夜里睡在炕上,是六角钱,若再掏一元,能包皮吃包皮喝,尽您享用。哪火炕边,立即会煨上柿子酒,烤上拳头大的洋芋。壹个时辰后,从火里刨出来,一剥开皮,一股喷鼻香味,吃上两口,便干得喉咙发噎,须主人捶一阵后背,千叮咛万叮咛慢慢来吃。吃毕洋芋,旅人们已经连连打嗝儿了,主人就取了碗来,盛满柿子酒让您。您一起始开端说不会喝,也就罢了,若接住了,喝了一碗,必要再喝二碗。柿子酒虽不暴烈,可是一碗下肚,已是腹热脸红,要推托时,主人会变了脸,说您看不起他她。喝了二碗,媳妇又来敬酒,她一碗,您一碗,您不能失了男子汉的脸面,喝下去了,您便醉了八成,舌头都有些硬了。
天黑了,主人会让旅人睡在炕上,媳妇会抱一床新被子,换了被头,换了枕巾。只说人家年轻夫妇要到另外的地方去睡了,可是关了门,主人脱鞋上了炕,媳妇也脱鞋上了炕,只是主人睡在中间,作了界墙而已。刚睡下,或许炕头上的喇叭就响了,要么是叫主人去开分地包皮产会,要么是主人去开党员家庭生活状态会。主人起来了,地穿衣服,末了把油灯点着。他她要出门,旅人也醒了,赶忙就起来穿衣,主人说:睡您的,俺开完会就回来,旅人肯定要说出什么话来,主人用眼光制止了。
"您是学过习的?"主人要这么说。
"学过习的?"旅人疑惑不解。
主人便将一条扁担放在炕中间。旅人看透了,闭了眼睛睡眠。哪灯耀得睡不着,媳妇不去吹,他她也不敢动身去吹,灯光下。媳妇看着他她,眼睛活得要谈话。旅人就赶忙合上眼,可是入不了梦,觉得身上有什么动。伸手一摸。肉肉的,忙丢进炕下的火坑,轻轻地"叭"了一声。壹个钟头,炕热得有些烫,可是不敢起身,只好翻来覆去,如烙烧饼一般。正难受着,主人回来了,看看炕上的扁担,看看旅人,就端了一碗凉水来让您喝。您喝了,他她放心了您,拿了酒又让您喝,说您真是学过习的人。您若不喝,说您必是有对不起人的事,一顿好打,赶到门外,您哪放在炕上的行李就休想再带走。重新睡下了,旅人还是烙得不行。主人会将一页木板垫在褥下,您就会睡得十分地舒服。可是到黎明炕便要凉了,凉得像一块冰,需得起来穿了衣服再睡不可。
天亮起来,旅人便像亲人一致被招待了,您问哪猪圈墙上,为什么画哪么多白灰圈儿?他她会告诉说,冬天狼多,夜里常来叼猪,可是却最怕这白圈儿,夜里没有听到狼嗥吗?旅人说未听见,也许是睡得太死了。他她就会又说,夜里出来解手,常会遇见这东西的,它会装着妇人的哭声呢。旅人听得直吐舌头,说冬天在这里投宿真不是轻松事。主人便又说,夏天的夜里哪才怕人呢,半夜里,床下有吱吱声,一揭褥子,下边便有一条彩花蛇的。旅人吓得噤了声。主人却说:"没事,抓起来从窗口甩出去就是了。"接着嘿嘿一笑,好似随便得很。
假如雪还在下,假如前边的麻街岭道还没有修起,旅人们就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了。哪么,主人们就会领您夜里去放狐子药。天明去收药,或许,只能见到狐子的脚印,还有的是狐子竟将哪用鸡皮包皮裹的烈性炸药轻轻用土埋了,可是经常常常是会丰收到被炸死的狐狸的。一起拿回来,将皮剥下,吃肉是没了疑问,就是旅人看中了哪狐皮,一阵讨价还价,生意也便作成了。
"您带有书吗?"
他她们老是这么问。一旦知道您是带了书的人,就怎样缠住您,要以狐皮换书,他她们就会去叫来小弟小妹,儿子,女儿,翻您的书捆。小孩子们最喜爱高考复习资料书,一换到手,就拿到火炕边入迷地读了。
清早起来随便往每一个人家里走走,就会发现哪晚辈的人和他她们的父老不同:老一辈人爱土地,小一辈人最恋书。小的全不穿大裆裤,不扎裹腿,不剃光头,都一身咔叽,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早晚必须要刷牙,一嘴的白沫。作父母的就要对旅人说:
"赶明日道通了,您们把这干净鬼也带去吧!"
说完,就作个谑笑,又说:
"刷刷就是了,哪嘴里有屎吗?快去看您的书,依靠好好学,咱们养您一辈子也行,若作样子,就收拾了,帮俺去卖些吃喝,一天也可赚四元五元哩!"
旅人已经和这里山民交上朋友了,什么话也就能说得来了。
"您们脚上的皮鞋走道不绊石头吗?"
"城里的道没有石头。"
"真好,半年都穿不烂哩。"
"能穿二三年的。您们也能穿嘛。"
"怕脚带不动。赶明日到了县上,该买台收音机了。"
"您们口袋里真有钱哩。"
"有什么呀,只是手上活泛些了。"
说到这儿,他她们就神秘起来,俯过身要问:
"您们在城里,离政策近,说说,这政策不会变了吧?"
"变不了啦!"
"真的?"
"真的!"
他她们就唠叨起来,说这黑龙口是商州最贫困的地方,过了麻街岭,沿川下去,哪里才叫富呢,夏里秋里收得好,副业也多,赚钱的门道多哩。
"咱们这穷地方,必须要好好干几年,要不您们城里人来,光笑话咱们了。"
从山沟下来,道过冰冻的河,又会碰见哪个捡粪的老汉了。谈开来,他她说他她是个孤老,在公道边修了四个厕所,专供旅人们用的。哪粪池十天半月就满了,他她便出售给各家,八分钱一担。光这一致收入,就够他她花费了,老汉很乐观,和旅人谈得投机,见一媳妇抱了小孩过来,就把小孩撑在手上,让立楞楞,然后逗弄小孩的小牛牛,说:
"小子,好好长!爷爷这辈子是完了,就看您们了,噢!"
他她乐滋滋笑着,逗弄着,惬意得像喝了(www,ajml,cn)一罐子醇美的酒,眼里是几分感慨,几分得意,又几分羡慕和嫉妒。有好事的旅人忙用照相机摄了这镜头,说要给这照片题名"希望"。
麻街岭的道终于修通了。旅人们坐车要离开了,头都伸出车窗,还是一眼一眼往后看着这黑龙口。
黑龙口就是怪,一来就觉得有味,一走就再也不能遗忘。司机却说:
"要去商州,这才是壹个门口儿,有趣的地方还在前边呢!"
朋友们美女们帅哥们今天关于励志演讲的的句子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看完了给个赞希望能帮到大家。www.ajml.cn数十年的文坛,题材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过去是,现在变个法儿仍是,以此走红过许多人。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 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 孙犁不是个写史诗的人(文坛上常常把史诗作家看得过重,那怎么还有史学家呢?),但他的作品直逼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 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 贾平凹:孙犁论,经典深度好文,优美简短的散文,深度好文章大全,经典短篇散文。
转载请注明:就爱造句网-好句子大全-句子网-在线词语造句词典 » 贾平凹经典美文,黑龙口
本站造句/句子文章《贾平凹经典美文,黑龙口》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此句子由网友整理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