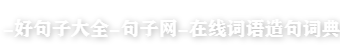朱自清:阿河
俺这一回寒假,因为所以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哪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微有皱痕;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哪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每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道。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俺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隙地上,或罗列着盆栽,或种莳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蟠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
俺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壹个女儿。她在外边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她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逮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咱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俺吃了饭,便是壹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俺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俺,她母亲要给她们找壹个好好的女用人;长工阿齐说有壹个表妹,母亲叫他她明天就带来作作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俺只是不经意地答应。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壹个小小的厨房。俺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能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俺偶然向外看看,见壹个面生的女用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甚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致。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俺,女用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俺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作么?”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俺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往后每日早上,中上,夜晚,俺经常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望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地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俺说,您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俺和娘说,把俺前年在家穿的哪身棉袄裤给了她吧。俺嫌哪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每当今拿出来让她穿,正合式呢。咱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俺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应该是您们教她的。好!您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朋友们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所以江浙的兵事,咱们的校园一时还不能开学。咱们朋友们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河如换了壹个人。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俺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帖。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俺几乎是壹个奇迹;俺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俺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俺生平所仅见!俺觉得咱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可是俺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
这是元宵节的前一夜晚。俺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哪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河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近了俺。她站在俺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您知道铅笔刨在哪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俺看。俺不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俺用手指着南边柱子。可是俺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俺领她走近了柱子。这时俺像闪电似地踌躇了一下,便说,“俺……俺……”她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俺。俺放进刨子里刨给她看。刨了两下,便想交给她;可是终于刨完了一支,交还了她。她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俺。俺窘极了。刹哪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刨好了。”俺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可是俺的头刚低下,俺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地从容地问道,“您会么?”她不曾掉过头来,只“嘤”了一声,也不谈话。俺看了她背影一会。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俺再抬起头来时,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总是望前看的;俺想再问她一句话,可是终于不曾出口。俺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便回到自个屋里。
俺一样想着些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见她往厨房里走时,俺发愿俺的眼将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哪几步道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俺臆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俺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致。不止她的腰,俺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哪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能掐出水来;俺的日记里说,“俺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俺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俺的脑海里。俺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么?哪么,她微笑的时间时候,便是盛开的时间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可是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俺不曾闻着少些儿香。唉!从前俺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俺真太对不起这样壹个人儿了。
午饭后,韦君照例地睡午觉去了,只有俺,韦小姐和其他她三位小姐在书房里。俺有意无意地谈起阿河的事。俺说:
“您们怎知道她的志气好呢?”
“哪天咱们教给她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聪明,就问她为甚么不念书?她被咱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
“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泪呢。”
哪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您们尽闹着玩儿!让俺说完了呀——”“俺代您说啵,”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壹个爹,没有娘。嫁了壹个男人,倒有三十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疱!他她是李妈的邻舍,俺还看见过呢。……”“好了,底下俺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尽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几岁?”俺问。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
“不,十八,俺知道,”韦小姐改正道。
“哦。您们可曾劝她离婚?”
“怎么不劝;”韦小姐应道,“她说十八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
“您们教她的好事,该每当何罪!”俺笑了。
她们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俺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俺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给阿齐拦住。他她们只是央告,阿齐只是不肯。这时韦君已走出院中,向他她们道,
“您们回去吧。人在俺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俄延了一会,只好走了。俺问韦君什么事?他她说,
“阿河啰!还不是瞎吵一回子。”
俺想他她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她小姐的好;咱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吃了饭,俺赶紧问韦小姐,她说,
“她是告诉娘的,您问娘去。”
俺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俺问,便笑着说,
“您要问这些事作什么?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她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她抢回去过了一夜。每当今早上,她骗她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她男人就会信她,派了两个人跟着。哪知她到了这里,便叫阿齐拦着哪跟来的人;她自个便跪在俺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她男人家去。您说俺有什么法子。只好让哪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她们要上学了,俺将来交给她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壹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您不知道;俺家三叔前儿来,俺还听他她说呢。俺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您想她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什么道理?家里只有壹个单身的老子;您想哪该死的老畜生!他她舍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么?”韦太太惊诧地问。
“他她们说得千真万确的。俺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每当今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您想现在还成什么地球!”
“这该不至于吧。”俺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爷,您哪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她快些走吧;别将咱们的运气带坏了。她的事,咱们往后也别谈吧。”
开学的通告来了,俺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夜晚,阿河忽然不到厨房里挈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地告诉俺,“娘叫阿齐将阿河送回去了;俺在楼上,都不知道呢。”俺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壹个人!而且俺觉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哪一夜俺是没有好好地睡,只翻来覆去地作梦,醒来却又一例茫然。这样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懒懒地向韦君夫妇和韦小姐告别而行,韦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俺只得含糊答应着。出门时,俺很想回望厨房几眼;可是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俺,俺怎好回头呢?
到校一打听,老友陆已来了。俺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她,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她。他她本是个好事的人;听俺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她只十八岁时,他她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
“可惜俺早有了俺哪太太!要不然,俺准得想法子娶她!”
“您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
俺俩默默相对了一会,陆忽然拍着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么?他她现在还没有主儿,何不给他她俩撮合一下。”
俺正要答说,他她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她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
“俺和他她说,他她不信;要问您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咱们凭什么去管!”俺说。
“想法子呀!”陆嚷着。
“什么法子?您说!”
“好,您们尽和俺开玩笑,俺才不理会您们呢!”汪笑了。
咱们几乎每日都要谈到阿河,可是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
一转眼已到了春假。俺再到韦君别墅的时间时候,水是绿绿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俺却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么样了。哪时韦小姐已回来两天。俺背地里问她,她说,“奇得很!阿齐告诉俺,说她二月间来求娘来了。她说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她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块钱来,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她自个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说她的爹哪有这些钱?她求娘可怜可怜她!娘的脾气您知道。她是个古板的人;她数说了阿河一顿,壹个钱也不给!俺现在和阿齐说,让他她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她,俺能给她五块钱。俺想您也能帮她些,俺教阿齐一块儿告诉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咱们这儿来啰!”
“俺拿十块钱吧,您告诉阿齐就是。”
俺看阿齐空闲了,便又去问阿河的事。他她说,
“她的爹正给她东找西找(www,ajml,cn)地找主儿呢。只怕难吧,八十块大洋呢!”
俺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
过了两天,阿齐从镇上回来,说,
“每当今见着阿河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作老板娘娘了!据说是自个拣中的;这种年头!”
俺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齐,似乎想在他她脸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俺说什么好呢?愿命运之神长远庇护着她吧!
第二天俺便托故离开了哪别墅;俺不愿再见哪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哪间小小的厨房!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一日作
朋友们美女们帅哥们今天关于励志演讲的的句子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看完了给个赞希望能帮到大家。www.ajml.cn关于拨用巨款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有一家报纸上曾经有过微词,好像说在这个战乱和饥饿的时代,不该忙着办这些事来粉饰, 旧书的危机指的是木版书,特别是大部头的。一年来旧书业大不景气。有些铺子将大部头的木版书论斤的卖出去造还魂纸。这自然, 至于毛笔,命运似乎更坏。跟"水笔"相比,它的不便更其显然。用毛笔就得用砚台和墨,至少得用墨盒或墨船(上海有这东西,, 几个月,北平的报纸上除了战事、杀人案、教育危机等等消息以外,旧书的危机也是一个热闹的新闻题目。此外,北平的文物,主, 朱自清:文物·旧书·毛笔,经典深度好文,优美简短的散文,深度好文章大全,经典短篇散文。
转载请注明:就爱造句网-好句子大全-句子网-在线词语造句词典 » 朱自清经典美文,阿河
本站造句/句子文章《朱自清经典美文,阿河》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此句子由网友整理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