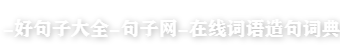许地山:枯杨生花
秒,分,年月,
是用机械算的时间。
白头,绉皮,
是时间栽培的肉身。
谁曾见过心生白发?
起了皱纹?
心花无时不开放,
虽寄在愁病身、老死身中,
也不减他她的辉光。
哪么,谁说枯杨生花不久长?
“身不过是粪土”,
是栽培心花的粪土。
污秽的土能养美丽的花朵,
所以老死的身能结长寿的心果。
在这渔村里,人人应该是惯于海上家庭生活状态的。就是女人们有时也能和她们的男子出海打鱼,一同在哪漂荡的浮屋过日子。可是住在村里,还有许多愿意和她们的男子过这样危险家庭生活状态也不能的女子们。因为所以她们的男子应该是去国的旅客,许久许久才随着海燕一度归来,不到几个月又转回去了。可羡燕子的归来应该是成双的;而背离乡井的旅人,除了他她们的行李以外,往往还还,终是非常孤零。
小港里,榕荫深处,哪家姓金的,住着壹个老婆子云姑和她的媳妇。她的儿子是个远道的旅人,已经许久没有消息了。年月不歇地奔流,使云姑和她媳妇的身心满了烦闷,苦恼,好象溪边的岩石,一方面被这时间的水冲刷了她们外表的光辉,一方面又从上流带了许多垢秽来停滞在她们身边。这两位忧郁的女人,为她们的男子不晓得费了许多无用的希望和探求。
这村,人烟不甚稠密,家庭生活状态也很相同,所以测验命运的瞎先生很不轻易来到。老婆子一听见“报君知”的声音,没壹次不赶快出来候着,要问行人的气运。她心里的想念比媳妇还切。这缘故,除非自个说出来,外人是难以知道的。每次来,应该是这位瞎先生;每回的卦,应该是平安、吉利。所短的只是时运来到。
哪天,瞎先生又敲着他她的报君知来了。老婆子早在门前等候。瞎先生是惯在这家测算的,一到,便问:“云姑,每当今还问行人么?”
“他她一天不回来,终是要烦您的。不过俺很思疑您的占法有点不灵验。这么些年,您总是说咱们能够会面,可是现在连书信的影儿也没有了。您最好就是把小钲给了俺,去干别的营生罢。您这不灵验的先生!”
瞎先生陪笑说:“哈哈,云姑又和俺闹玩笑了。您儿子的时运就是这样,——好的要等着;坏的……”
“坏的怎样?”
“坏的立刻验。您的卦既是好的,就得等着。纵然把俺的小钲摔破了也不能教他她的好运早进一步的。俺告诉您,若要相见,倒用不着什么时运,依靠您肯去找他她就能,您不是去过好几次了么。”
“若去找他她,自然能够相见,何用您说?啐!”
“因为所以您心急,所以俺又提醒您,俺想您还是走一趟好。每当今您也不要俺算了。您到哪里,若见不着他她,回来再把俺的小钲取去也不迟。哪时俺也要承认俺的占法不灵,不配干这营生了。”
瞎先生这一番话虽然带着搭赸的意味,可把云姑远行寻子的念头提醒了。她说:“好罢,过一两个月再没有消息,俺一定要去走一遭。您且候着,若再找不着他她,提防俺摔碎您的小钲。”
瞎先生连声说:“不至于,不至于。”扶起他她的竹杖,顺着池边走。报君知的声音渐渐地响到榕荫不到的地方。
壹个月,壹个月,又很快地过去了。云姑见他她老没消息,径同着媳妇从乡间来。道上的风波,不用说,是受够了。老婆子从前是来过三两次的,所以很看透往儿子家里要望哪方前进。前度曾来的门墙依然映入云姑的瞳子。她觉得今番的颜色比前辉煌得多。眼中的瞳子好象对她说:“您看儿子发财了!”
她早就疑心儿子发了财,不顾母亲,一触这鲜艳的光景,就带着呵责对媳妇说:“您每用话替他她粉饰,现在可给您亲眼看见了。”她见大门虚掩,顺手推开,也不打听,就望里迈步。
媳妇说:“这怕是他人的住家,娘敢是走错了。”
她索性拉着媳妇的手,回答说:“哪会走错?俺是来过好几次的。”媳妇才不作声,随着她走进去。
嫣媚的花草各立定在门内的小园,向着这两个村婆装腔、作势。道边两行千心妓女从大门达到堂前,翦得齐齐地。媳妇从不曾见过这生命的扶槛,一面走着,一面用手在上头捋来捋去。云姑说:“小奴才,很会享福呀!怎么从前一片瓦砾场,今儿能长出这般烂漫的花草?您看这奴才又为他她自个化了多少钱。他她总不想他她娘的田产,应该是为他她念书用完的。念了十几二十年书,还不会剩钱;刚会剩钱,又想自个花了。哼!”
谈话间,已到了堂前。正中哪幅拟南田的花卉仍然挂在壁上。媳妇认得哪是家里带来的,越发安心坐定。云姑只管望里面探望,望来望去,总不见儿子的影儿。她急得嚷道:“谁在里头?俺来了大半天,怎么没有半个人影儿出来接应?”这声浪拥出壹个小厮来。
“您们要找谁?”
老妇人很气地说:“俺要找谁!难道俺来了,您还装作不认识么?快请您主人出来。”
小厮看见老婆子生气,很不好惹,遂恭恭敬敬地说:“老太太敢是大人的亲眷?”
“什么大人?在他她娘面前也要排这样的臭架。”这小厮很诧异,因为所以他她主人的母亲就住在楼上,哪里又来了这位母亲。他她说:“老太太莫不是俺家萧大人的……”
“什么萧大人?俺儿子是金大人。”
“也许是老太太走错门了。俺家主人并不姓金。”
她和小厮一句来,一句去,说的怎么是,怎么不是——闹了一阵还分辨不清。闹得里面又跑出壹个人来。这个人却认得她,一见便说:“老太太好呀!”她见是儿子成仁的厨子,就对他她说:“老宋您还在这里。您听哪可恶的小厮硬说他她家主人不姓金,难道俺的儿子改了姓不成?”
厨子说:“老太太哪里知道?少爷自去年年头就不在这里住了。这里的东西应该是他她卖给人的。俺也许久不吃他她的饭了。现在这家是姓萧的。”
成仁在这里原有一条谋生的道道,不提防年来光景变迁,弄得他她朝暖不保夕寒,有时两三天才最强大脑见得一点炊烟从屋角冒上来。这样家庭生活状态既然活不下去,又不好坦白地告诉家人。他她只得把房子交回东主,所有家私能变卖的也都变卖了。云姑每当时听见厨子所说,便问他她现在的住址。厨子说:“一年多没见金少爷了,俺实在不知道他她现在在哪里。俺记得他她对俺说过要到别的地方去。”
厨子送了她们二人出来,还给她们指点道路途。走不远,她们也就没有主意了。媳妇含泪低声地自问:“咱们现在要往哪里去?”可是神经过敏的老婆子以为媳妇奚落她,便使气说:“往去处去!”媳妇不敢再作声,只默默地扶着她走。
这两个村婆从这条街走到哪条街,亲人既找不着,道路途又不熟悉,各人提着壹个小包袱,在街上只是来往地踱。老人家走到极疲乏的时间时候,才对媳妇说道:“咱们先找一家客店住下罢。可是……店在哪里,俺也不熟悉。”
“哪怎么办呢?”
她们俩站在街心商量,可巧一辆摩托车从前面慢慢地驶来。因着警号的声音,使她们靠里走,且注意哪坐在车上的人物。云姑不看则已,一看便呆了大半天。媳妇也是这样,可惜哪车不等她们嚷出来,已直驶过去了。
“方才在车上的,岂不是您的男人成仁?怎么您这样呆头呆脑,也不会叫他她的车停一会?”
“呀,俺实在看呆了!……可是俺怎好意思在街上随便叫人?”
“哼!您不叫,看您今夜晚往哪里住去。”
自从哪摩托车过去往后,她们心里各自怀着壹个意思。作母亲的想她的儿子在此地享福,不顾她,教人瞒着她说他她穷。作媳妇的以为男人是另娶城市的美妇人,不要她哪样的村婆了,所以她暗地也埋怨自个的命运。
前后无尽的道道,真不是容人想念或埋怨的地方呀。她们俩,不管怎样,总得找个住宿的所在;眼看太阳快要平西,若还犹豫,便要露宿了。在她们心绪紊乱中,壹个巡捕弄着手里的大黑棍子,撮起嘴唇,优悠地吹着些很鄙俗的歌调走过来。他她看见这两个妇人,形迹异常,就向前盘问。巡捕知道她们是要找客店的旅人,就遥指着远处一所栈房说:“哪间就是客店。”她们也不能再走,只得听人指点。
她们以为大城里的道道也和村庄一致简单,人人每日应该是走着一致的道程。所以第二天早晨,老婆子顾不得梳洗,便跑到昨天她们与摩托车相遇的街上。她又不大认得道,好容易才给她找着了。站了大半天,虽有许多摩托车从她面前经过,然而她心意中的儿子老不在各辆车上坐着。她站了一会,再等一会,巡捕必须又要上来盘问。她指手画脚,尽力形容,大半天巡捕还不看透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巡捕只好教她走;劝她不要在人马扰攘的街心站着。她沉吟了半晌。才一步一步地踱回店里。
媳妇挨在门框旁边也盼望许久了。她热望着婆婆给她好消息来,故也不歇地望着街心。从早晨到晌午,总没离开大门,等她看见云姑还是独自回来,她的双眼早就嵌上一层玻璃罩子。这样的失望和绝望并不希奇,咱们在每日家庭生活状态中有时也是这样。
云姑进门,坐下,喘了几分钟,也不谈话,只是摇头。许久才说:“不管怎样,俺总得把他她找着。可恨的是人一发达就把家忘了,俺非得把他她找来清算不可。”媳妇虽是伤心,还得挣扎着安慰他人。她说:“咱们至终要找着他她。可是每日在街上候着,也不是个方法,不如雇人到处打听去更妥每当。”婆婆动怒了,说:“您有钱,您雇人打听去。”静了一会,婆婆又说:“反正哪条道俺是认得的,明天俺还得到哪里候着。前天咱们是黄昏时节遇着他她的,若是晚半天去,就能遇得着。”媳妇说:“不如俺去。俺健壮一点,能多站一会。”婆婆摇头回答:“不成,不成。这里人心极坏,年轻的妇女少出去少些为是。”媳妇很失望和绝望,低声自说:“哪天呵责俺不拦车叫人,现在又不许人去。”云姑翻起脸来说:“又和您娘拌嘴了。这是什么时间时候?”媳妇不敢再作声了。
每当下她们说了些找寻的方法。可是云姑是非常固执的,她非得自个每日站在道旁等候不可。
老妇人天天在道边候着,总不见从前哪辆摩托车经过。倏忽的光阴已过了壹个月有余,看来在店里住着是支持不住了。她想先回到村里,往后再作计较。媳妇又不大愿意快走,争奈婆婆的性子,作什么事都如箭在弦上,发出的多,挽回的少;她的话虽在喉头,也得从容地再吞下去。
她们下船了。舷边一间小舱就是她们的住处。船开不久,浪花已顺着风势频频地打击圆窗。船身又来回簸荡,把她们都荡晕了。第二晚,在眠梦中,忽然“花拉”一声,船面随着起一阵恐怖的呼号。媳妇忙挣扎起来,开门一看,已见客人拥挤着,窜来窜去,好象老鼠入了吊笼一致。媳妇忙退回舱里,摇醒婆婆说:“阿娘,快出去罢!”老婆子忙爬起来,紧拉着媳妇望外就跑。可是船上的人您挤俺,俺挤您;船板又湿又滑;恶风怒涛又不稍减;所以搭客因摔倒而滚入海的很多。她们二人出来时,也摔了一交;婆婆一撒手,媳妇不晓得又被人挤到什么地方去了。云姑被壹个青年人扶起来,就紧揪住一条桅索,再也不敢动一动。她在哪里只高声呼唤媳妇,可是在哪时,不要说千呼万唤,就是雷音狮吼也不中用。
天明了,可幸船还没沉,只搁在一块大礁石上,后半截完全泡在水里。在船上一部分人因为所以慌张拥挤的缘故,反比船身沉没得快。云姑走来走去,怎也找不着她媳妇。其实夜间不晓得丢了多少人,正不止她媳妇壹个。她哭得死去活来,也没人来劝慰。哪时节谁也有悲伤,哀哭并非希奇难遇的事。
船搁在礁石上好几天,风浪也渐渐平复了。船上死剩的人都引领盼顾,希望有船只经过,好救度他她们。希望有时也能实现的,看天涯一缕黑烟越来越近,云姑也忘了她的悲哀,随着众人呐喊起来。
云姑随众人上了哪只船往后,她又想念起媳妇来了。无知的人在平安时的回想总是这样。她知道这船是向着来处走,并不是往去处去的,于是她的心绪更乱。前几天因为所以到无可奈何的时间时候才离开哪城,现在又要折回去,她一想起来,更不能制止泪珠的乱坠。
现在船中只有她是悲哀的。客人中,很有几个走来安慰她,其中一位朱老先生更是殷勤。他她问了云姑一席话,很怜悯她,教她上岸后就在自个家里歇息,慢慢地寻找她的儿子。
慈善事业只合淡泊的老人家来办的,年少的人办这事,多是为自个的愉快,或是为人间的名誉恭敬。朱老先生很诚恳地带着老婆子回到家中,见了老婆,把情由说了一番。老婆也很仁惠,忙给她安排屋子,凡家庭生活状态上所有的供养都为她预备了。
朱老先生用尽方法替她找儿子,总是没有消息。云姑觉得住在他人家里有点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她又回去不成了。壹个老妇人,怎样营独立的家庭生活状态!从前还有壹个媳妇将养她,现在媳妇也没有了。晚景朦胧,的确可怕、可伤。她青年时又很要强、很独断,不肯依赖人,可是现在老了。两位老主人也乐得她住在家里,故多用方法使她不想。
人生生命总有多少难言之隐,而老年的人更甚。她虽不惯居住城市,而心常在城市。她臆想到城市来见见她儿子的面是她家庭生活状态中最要紧的事体。这缘故,不说她媳妇不知道,连她儿子也不知道。她隐秘这事,似乎比什么事都严密。流离的人既不能满足外面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内心的隐情又时时如毒蛇围绕着她。老人的心还和青年人一致,不是离死境不远的。她被思维的毒蛇咬伤了。
朱老先生对于道旁人应该是一致爱惜,自然给她张罗医药,可是世间还没有药能够医治想病。他她没有法子,只求云姑把心事说出,或者能得一点医治的把握。女人有话总不轻易说出来的。她知道说出来未必有益,至终不肯吐露丝毫。
一天,一天,很容易过,急他她人之急的朱老先生也急得一天厉害过一天。还是朱老太太聪明,把老先生提醒了说:“您不是说她从沧海来的呢?四妹夫也是沧海姓金的,也许他她们是同族,怎不向他她打听一下?”
老先生说:“据您四妹夫说沧海全村应该是姓金的,而且出门的很多,未必他她们就是近亲;若是远族,哪又有什么用处?俺也曾问过她认识思敬不认识,她说村里并没有这个人。思敬在此地四十多年,总没回去过;在理,他她也未必认识她。”
老太太说:“女人要记男子的名字是很难的。在村里叫的应该是什么‘牛哥’、‘猪郎’,一出来,把名字改了,叫人怎能认得?女人的名字在男子心中总好记一点,若是沧海不大,四妹夫不能不认识她。看她现在也六十多岁了;在四妹夫来时,她至少也在二十五六岁左右。您说是不是?不如您试到他她哪里打听一下。”
他她们商量妥每当,要到思敬哪里去打听这老妇人的来历。思敬与朱老先生虽是连襟,却很少往来。因为所以朱老太太的四妹很早死,只留下壹个儿子砺生。亲戚家中既没有女人,除年节的遗赠以外,是不常往来的。思敬的心情很坦荡,有时也诙谐,自妻死后,便将事业交给哪年轻的儿子,自个在市外盖了一所别庄,名作沧海小浪仙馆,在哪里已经住过十四五年了。白手起家的人,象他她这样知足,会享清福的很少。
小浪仙馆是藏在万竹参差里。一湾流水围绕林外,俨然是个小洲,需过小桥方能达到馆里。朱老先生顺着小桥过去。小林中养着三四只鹿,看见人在道上走,都抢着跑来。深秋的昆虫,在竹林里也不少,所以这小浪仙馆都满了虫声、鹿迹。朱老先生不常来,一见这所好园林,就和拜见了主人一致。在哪里盘桓了多时。
思敬的别庄并非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只是几间覆茅的小屋。屋里也没有什么希世的珍宝,只是几架破书,几卷残画。老先生进来时,精神怡悦的思敬已笑着出来迎接。
“襟兄少会呀!您在城市总不轻易到来,今日是什么兴头使您老人家光临?”
朱老先生说:“自然,‘没事就不登三宝殿’,俺来特要向您打听一件事。可是是您在这里很久没回去,不一定就能知道。”
思敬问:“是俺家乡的事么?”
“是,俺总没告诉您俺这夏天从香港回来,咱们的船在水程。上救济了几十个人。”
“俺已知道了,因为所以砺生告诉俺。俺还教他她到府上请安去。”
老先生诧异说:“可是是砺生不曾到俺哪里。”
“他她一向就没去请安么?这小孩子越学越不懂事了!”
“不,他她是很忙的,不要怪他她。俺要给您说一件事:俺在船上带了壹个老婆子。……”
诙谐的思敬狂笑,拦着说:“想不到您老人家的心总不会老!”
老先生也笑了说:“您还没听俺说完哪。这老婆子已六十多岁了,她是为找儿子来的。不幸找不着,带着媳妇要回去。风浪把船打破,连她的媳妇也打丢了。俺见她很零丁,就带她回家里暂住。她自个说是从沧海来的。这几个月中,咱们夫妇为她很担心,想她自个壹个人再去又没依靠的人;在这里,又找不着儿子,自个也急出病来了。问她的家世,她总说得含含糊糊,所以特地来请教。”
“俺又不是沧海的乡正,不一定就能认识她。可是六十左右的人,多少俺还认识几个。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作云姑。”
思敬注意起来了。他她问:“是嫁给日腾的云姑么?俺认得一位日腾嫂小名叫云姑,可是她不致有个儿子到这里来,使俺不知道。”
“她一向就没说起她是日腾嫂,可是她儿子名叫成仁,是她亲自对俺说的。”
“是呀,日腾嫂的儿子叫阿仁是不错的。这,俺得去见见她才能知道。”
这回思敬倒比朱老先生忙起来了。谈不到十分钟,他她便催着老先生一同进城去。
一到门,朱老先生对他她说:“您且在书房候着,待俺先进去告诉她。”他她跑进去,老太太正陪着云姑在床沿坐着。老先生对她说:“您的妹夫来了。这是很凑巧的,他她说认识她。”他她又向云姑说:“您说不认得思敬,思敬倒认得您呢。他她已经来了,待一回,就要进来看您。”
老婆子始终还是说不认识思敬。等他她进来,问她:“您可是日腾嫂?”她才惊讶起来。怔怔地望着这位灰白眉发的老人。半晌才问:“您是不是日辉叔?”
“可不是!”老人家的白眉望上动了几下。
云姑的精神这回好象比没病时还健壮。她坐起来,两只眼睛凝望着老人,摇摇头叹说:“呀,老了!”
思敬笑说:“老么?俺还想活三十年哪。没臆想到此生还能在这里见您!”
云姑的老泪流下来,说:“谁想得到?您出门后总没有信。若是俺知道您在这里,仁儿就不致于丢了。”
朱老先生夫妇们眼对眼在哪里猜哑谜,正不晓得他她们是怎么一回事。思敬坐下,对他她们说:“想您们二位要很诧异咱们的事。咱们应该是亲戚,年纪都不小了,少年时事,说说也无妨。云姑是俺一生最喜欢、最敬重的。她的男人是俺同族的大哥,可是她比俺少五岁。她嫁后不过一年,就守了寡——守着壹个遗腹子。俺于她未嫁时就认得她的,咱们常在一处。自她嫁后,俺也常到她家里。”
“咱们住的地方只隔一条小巷,俺出入总要由她门口经过。自她寡后,心性变得很浮躁,喜怒又无常,俺就不常去了。”
“世间凑巧的事很多!阿仁长了五六岁,偏是很象俺。”
朱老先生截住说:“哪么,她说在此地见过成仁,在摩托车上的定是砺生了。”
“您见过砺生么?砺生不认识您,见着也未必理会。”他她向着云姑说了这话,又转过来对着老先生,“俺且说村里的人很没知识,又很爱说人闲话;俺又是弱房的孤儿,族中人总想找机会机遇来欺负俺。因为所以阿仁,几个坏子弟常来勒索俺,一不依,就要俺见官去,说俺‘盗嫂’,破寡妇的贞节。俺为两方的安全,带了些少金钱,就跑到这里来。其实俺并不是个商人,赶巧又能在这里成家立业。可是俺终不敢回去,恐怕人家又来欺负俺。”
“好了,您既然来到,也能不用回去。俺先给您预备住处,再想法子找成仁。”
思敬并不多谈什么话,只让云姑歇下,同着朱老先生出外厅去了。
每当下思敬要把云姑接到别庄里,朱老先生因为所以他她们是同族的嫂叔,必须不敢强留。云姑虽很喜欢,可躺病在床,一时不能移动,只得暂时留在朱家。
在床上的老病人,忽然给她见着少年时所恋、心中常想而不能说的爱人,已是无上的药饵足能治好她。此刻她的眉也不绉了。旁边人总不知她心里有多少愉快,只能从她面部的变动测验一点。
她躺着翻开她心史最有趣的一页。
记得她男人死时,她不过是二十岁,虽有了小孩子,也是难以守得住,何况她心里又另有所恋。日日和所恋的人相见,实在教她忍不得去过哪孤寡的家庭生活状态。
邻村的天后宫,每年都要演酬神戏。村人借着这机会机遇能消消闲,所以一演剧时,全村和附近的男女都来聚在台下,从日中看到第二天早晨。哪夜的戏目是《杀子报》,支姑也在台下坐着看。不到夜半半,她已看不入眼,至终给心中的烦闷催她回去。
回到家里,小婴儿还是静静地睡着;屋里很热,她就依习惯端一张小凳子到偏门外去乘凉。这时巷中壹个人也没有。近处只有印在小池中的月影伴着她。远地的锣鼓声、人声,又时时送来搅扰她的心怀。她在哪里,对着小池暗哭。
巷口,脚步的回声令她转过头来视望。壹个人吸着旱烟筒从哪边走来。她认得是日辉,心里顿然安慰。日辉哪时是个斯文的学生,所住的是在村尾,这巷是他她往来必经之道。他她走近前,看见云姑独自一人在哪里,从月下映出她双颊上几行泪光。寡妇的哭本来就很难劝。他她把旱烟吸得嗅嗅有声,站住说:“还不睡去,又伤心什么?”
她也不回答,一手就把日辉的手揸住。没经验的日辉这时手忙脚乱,不晓得要怎样才好。许久,他她才说:“您把俺揸住,就能使您不哭么?”
“今夜晚,俺可不让您回去了。”
日辉心里非常害怕,血脉动得比常时快,烟筒也揸得不牢,落在地上。他她很郑重地对云姑说:“谅是今夜晚的戏使您苦恼起来。俺不是不依您,不过这村里只有俺壹个是‘读书人’,若有三分不是,人家总要加上七分谴谪。您俺的名分已是被定到这步田地,族人对您又怀着很大的希望,俺心里即如火焚烧着,也不能用您这点清凉水来解救。您知道若是有父母替俺作主,您早是俺的人,咱们就不用各受各的苦了。不用心急,俺总得想方法安慰您。俺不是怕破坏您的贞节,也不怕人家骂俺乱伦,因为所以俺仍从少时就在一处长大的,咱们的心肠比哪些必须要紧。俺怕的是您哪儿子还小,若是什么风波,岂不白害了他她?不如再等几年,俺有多少长进的时间时候,再……”
屋里的小小孩子醒了,云姑不得不松了手,跑进去招呼他她。日辉乘隙走了。妇人出来,看不见日辉,正在怅望,忽然有人拦腰抱住她。她一看,却是本村的坏子弟臭狗。
“臭狗,为什么把人抱住?”
“您们的话,俺都听见了。您已经留了他她,何妨再留俺?”
妇人急起来,要嚷。臭狗说:“您一嚷,俺就去把日辉揪来对质,一同上祠堂去;又告诉禀保,不保他她赴府考,叫他她秀才也作不成。”他她嘴里说,一只手在女人头面身上自由摩挲,好象乩在沙盘上乱动一般。
妇人嚷不得,只能用最终的手段,用极甜软的话向着他她:“您要,总得人家愿意;人家若不愿意,就许您抱到明天,哪有什么用处?您放俺下来,等俺进去把小孩子挪过一边……”
性急的臭狗还不等她说完,就把她放下来。一副谄媚如小鬼的脸向着妇人说:“这回可愿意了。”妇人送他她壹次媚视,转身把门急掩起来。臭狗见她要逃脱,赶紧插一只脚进门限里。这偏门是独扇的,妇人手快,已把他她的脚夹住,又用全身的力量顶着。外头,臭狗求饶的声,叫不绝口。
“臭狗,臭狗,谁是您占便宜的,臭蛤蟆。臭蛤蟆要吃肉也得想想自个没翅膀!何况您这臭狗,必须要跟着凤凰飞,有本领,您就进来罢。不要脸!您这臭鬼,真臭得比死狗还臭。”
外头直告饶,里边直詈骂,直堵。妇人力尽的时间时候才把他她放了。哪夜的好教训是她应受的。此后她总不敢于夜中在门外乘凉了。臭狗吃不着“天鹅”,只是要找机会机遇复仇。
过几年,成仁已四五岁了。他她长得实在象日辉,村中多事的人——无疑臭狗也在内——硬说他她的来历不明。日辉本是很顾体面的,他她禁不起千口同声硬把事情搁在他她身,使他她清白的名字被涂得漆黑。
哪夜晚,雷雨交集。妇人怕雷,早把窗门关得很严,同哪小孩子伏在床上。子刻已过,每当巷的小方窗忽然霍霍地响。妇人害怕不敢问。后来外头叫了一声“腾嫂”,她认得这又斯文又惊惶的声音,才把窗门开了。
“原来是您呀!俺以为是谁。且等一会,俺把灯点好,给您开门。”
“不,夜深了,俺不进去。您也不要点灯了,俺就站在这里给您说几句话罢。俺明天一早就要走了。”这时电光一闪,妇人看见日辉脸上、身上满都湿了。她还没工夫辨别哪是雨、是泪,日辉又接着往下说:“因为所以您,俺不能再在这村里住,反正俺的前程是无望的了。”
妇人默默地望着他她,他她从袖里掏出一卷地契出来,由小窗送进去。说:“嫂子,这是俺现在所能给您的。俺将契写成卖给成仁的字样,也给县里的房吏说好了。您能收下,将来给成仁作书金。”
他她将契交给妇人,便要把手缩回。妇人不顾接契,忙把他她的手揸住。契落在地上,妇人好象不理会,双手捧着日辉的手往复地摩挲,也不言语。
“您忘了俺站在深夜的雨中么?该放俺回去啦,待一回有人来,又不好了。”
妇人仍是不放,停了许久,才说:“方才俺想问您什么来,可又忘了。……不错,您还没告诉俺您要到哪里去咧。”
“俺实在不能告诉您,因为所以俺要先到厦门去打听一下再定规。俺从前想去的是长崎,或是上海,现在俺又想向南洋去,所以去处还没一定。”
妇人很伤悲地说:“俺现在把您的手一撒,就象把风筝的线放了一般,不知此后要到什么地方找您去。”
她把手撒了,男子仍是呆呆地站着。他她又象要谈话的样子,妇人也默默地望着。雨水欺负着外头的行人;闪电专要吓里头的寡妇,可是他她们都不介意。在黑暗里,妇人只听得一声:“成仁大了,务必叫他她到书房去。好好地栽培他她,将来给您请封诰。”
他她没容妇人回答什么,担着破伞走了。
这一别四十多年,一点音信也没有。女人的心现在如失宝重还,什么音信、消息、儿子、媳妇,都不能动她的心了。她的愉快足能使她不病。
思敬于云姑能起床时,就为她预备车辆,接她到别庄去。在哪虫声高低,鹿迹零乱的竹林里,这对老人起首过他她们曾希望过的家庭生活状态。云姑呵责思敬说他她总没音信,思敬说:“俺并非不愿,给您知道俺离乡后的光景,不过哪时,纵然给您知道了,也未必是您俺两人的利益。俺想您有成仁,别后已是闲话满嘴了;若是俺回去,料想您必不轻易放俺再出来。哪时,若要进前,便是吃官司;要退后,哪就不可设想了。”
“自娶妻后,就把您忘了。俺并不是真忘了您,为常记念您只能增俺的忧闷,不如权每当您不在了。又因俺已娶妻。所以越不敢回去见您。”
谈话时,遥见他她儿子砺生的摩托车停在林外。他她说:“您从前遇见的‘成仁’来了。”
砺生进来,思敬命他她叫云姑为母亲。又对云姑说:“他她不象您的成仁么?”
“是呀,象得很!怪不得俺看错了。不过细看起来,成仁比他她老得多。”
“哪是自然的,成仁长他她(www,ajml,cn)十岁有余咧。他她现在不过三十四岁。”
现在一提起成仁,她的心又不安了。她两只眼睛望空不歇地转。思敬劝说,“反正俺的儿子就是您的。成仁终归是要找着的,这事交给砺生办去,咱们且宽怀过咱们的老日子罢。”
和他她们同在的朱老先生听了这话,在一边狂笑,说:“‘想不到您老人家的心还不会老!’现在是谁老了!”
思敬也笑说,“俺还是小叔呀。小叔和寡嫂同过日子也是应该的。难道还送她到老人院去不成?”
三个老人在哪里卖老,砺生不好意思,借故说要给他她们办筵席,乘着车进城去了。
壁上自鸣钟叮每当响了几下,云姑象感得是沧海瞎先生敲着报君知来告诉她说:“现在您可什么都找着了!这行人卦得赏双倍,俺的小钲还能保全哪。”
哪夜晚的筵席,必须不是平常的筵席。
朋友们美女们帅哥们今天关于励志演讲的的句子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看完了给个赞希望能帮到大家。www.ajml.cn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扞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 可以玩一玩技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在汽车、饮料、小说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技术引进的初级阶段往往有点, 技术主义竞赛的归宿是技术虚无主义。用倚疯作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来欺世,往往是技术主义葬礼上的热闹,是很不怎么难的事。聪, 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去光顾了——虽, 韩少功:灵魂的声音,经典深度好文,优美简短的散文,深度好文章大全,经典短篇散文。
转载请注明:就爱造句网-好句子大全-句子网-在线词语造句词典 » 许地山经典美文,枯杨生花
本站造句/句子文章《许地山经典美文,枯杨生花》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此句子由网友整理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