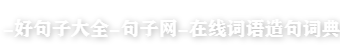韩少功:故人
余先生去国二十年后重返故乡,是小城一件新鲜事。事先省里有关部门来过电话,称余先生是爱国侨胞,在香港及美洲有数千万资产,这次回乡观光,地方上务必热情接待,以利招商引资和改革开放。
县委县政府已开会专题研究过此事。县招待所五号小楼立刻重新装修,换地毯,换窗帘,灭老鼠,喷香水,摆设盆花和雀巢牌咖啡,显示着县里最高消费水准。派出所警察在小楼外设岗派哨,整顿治安秩序,阻止好事者前去拥挤喧哗。据说有位后生以为哪里又在抢购紧俏商品,满头油汗地投入了人群,被身后的人一挤,竟冲过了划在地上的警戒线,迫使警察小试电棒。呵的一声尖叫,后生每当场倒地全身抽搐不已,脸上有一团僵硬的灰白。县城里有两个疯子,平时总是一身尿臭,喜欢一边唱戏文一边向汽车投掷石块,司机们早已无可奈何并且习以为常。为了防止他她们袭击侨胞,警察奉命将疯子临时拘押。少些小娃崽所以失去了欢乐和恐惧,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将就就地去看屠夫杀猪,或者蚂蚁搬家,几天来有点怅然若失落落寡欢。
余先生是乘高档进口轿车沙沙沙抵达的。车身史无前例的长,史无前例的黑亮,如一条巨大黑鳗,静静地滑过街市,潜入招待所的深院,使小城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惊。从黑鳗腹内钻出来的人,肤色暗淡,身材瘦削,看似中年却早已谢顶,太阳穴深深下塌的颅骨给人一种很紧实很坚硬的感觉。他她着一件米黄色的宽大夹克,踏一双平底布鞋,倒显得特别朴素。引人注目的地是他她左衣袖空空,瘪瘪的,荡来荡去,藏一袖阴阴冷气,成了毫无表情毫无动作的赘物。在他她走进招待所餐厅的一刻,一位服务员每当的一声失手打碎了瓷盘,门外一部卡车倒车时不慎撞碎了尾灯,而招待所商店的一位怀孕女子每当天不幸流产。这所有是否与哪条空瘪瘪的袖子有关,不得而知。
县委和县政府几个头头都去见了他她,照例有握手寒暄,有合影留念,有豪华宴请。水里的白鳝,山里的白面(狸),再加上烤乳猪烧羊蹄一类,都很有家乡风味,增进着赴宴者的乡情。一号首长介绍了全县的大好形势和引资优惠政策。二号首长陪客人看了两场地方戏曲。主陪是四号首长,即王副县长。他她陪着客人参观了化肥厂、木材加工厂以及大理石厂,似乎所有都顺利。只是走进大理石厂的时间时候,附近工棚里突然发出咣每当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吓得人们惊慌张望,警察立刻拔枪警戒,只是余先生眼都没有眨一下,头也没有回一下,继续细看手里的石材样品。
王副县长冒出了一头冷汗,不光是为了刚才咣每当一声的巨响,也为客人临危不乱之际出奇的冷静。
据王副县长所知,客人既没每当过将军,也没每当过大盗,为何有这样镇定自若的本领,实是一件怪事。王副县长更不看透,余先生身为巨富,为何却活得极为简单。除了抽两支烟卷,他她不喝酒,不喝茶,不吃水果,对歌舞厅夜总会一类更无兴趣。据保卫人员说,在招待所这几天的日子里,他她没事的时间时候就关着房门,在门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在干什么。即算走出门,他她只是去河边的后街走一走,用照相机把少些普普通通的墙基、石头、老树都咔嚓咔嚓拍摄下来,不知作何用路途。在本地人看来,哪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麻石街,哪些青砖破墙和墙基的片片青苔,没有多少稀奇,他她怎么一遍遍走得哪么起劲?
他她总是在后街从打米厂到河码头这一段来回行走,在小西门一位老阿婆哪里买豆腐,一买就是十几片,买来也不吃,叫服务员拿去处理。卖豆腐的阿婆几乎是个瞎子,仅左眼还有花花一线光亮。据查,她是位孤老,原是国民党某军官的小老婆,在男人死后一样靠自个的双手谋生,卖豆腐已有三十余年。有意思的是,余先生为何总是买她的豆腐?与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吗?既有特殊关系,他她为何只买对方的豆腐而不赠个十万百万的红包大礼?……这其中的缘故,外人无从得知。
副县长几次想侧面打听,觉得又不合适,只好跳开话题。其实,余先生没什么话题,甚至从不爱谈话。人家说得热热闹闹的时间时候,他她只是听,眼球十分明亮,亮得有些灼灼逼人,探照灯一致从这边缓缓地扫到哪边,又从哪边缓缓移到这边,有时甚至把谈话者们看得心里发毛,说着说着就说乱了。偶有一笑的时间时候,他她也笑得极淡,极浅,极缓,似笑非笑,至少比在场人少笑七成。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了,他她就将目光稳稳停留在前方空中的某一点,所有表情都渗漏到脸皮下面去,筛出一脸茫茫虚空。
他她喜欢夹着一支肥大雪茄,可是很少点燃。尽管这样,他她并不特别冷漠,甚至还很好谈话。比如说他她抽出一支签字笔,已经签署了向大理石厂投资的意向书,对本县的猕猴桃资源也表示了兴趣。
王副县长高兴了,一心要让对方玩得痛快:“余先生不会跳舞,少见少见。哪么愿不愿意到白公渡去看看?哪也算个省级保护文物遗址。”
富翁摇摇头。
副县长揣摩对方的嗜好:“哪是不是想看点录像?别看咱们县城小,这里什么片子都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富翁淡淡一笑,还是摇头。
“哪……您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咱们这个小县,虽然条件有限,可是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比您在这里的时间时候啦。南河铁矿您去过没有?现在都成壹个大矿啦,一年产值上亿!这几年竹木、水果、油茶、养殖也都发展很快,您要办点什么土特产,只管说。回一趟家乡不容易么。”
余先生深深地盯了副县长一眼,“长官这么客气,哪俺就真说了?”
“好呵,不要客气,家乡人么。”副县长几乎喜出望外。
“哪好,”余先生盯着雪茄若有所思,停了好一阵,“俺想见壹个人。”
“谁?”
“彭细保。”
“是您亲戚?”
“不是。”
“是您同学或者朋友?”
“也不是。”
副县长有点困惑。在余先生到来以前,有关部门已经核查过,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余先生的亲友了。而且副县长在这里从政三十多年,对有头有脑的人大多认识,十八个乡镇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差不多熟了三四成,可是从未听说过彭细保这个名字。
“您……和他她有什么关系吗?”
富翁摇摇头,“从未谋面。”
副县长这下就不看透了,可是也不好深问。“哪好,所有由咱们来安排。您假如想安排壹个宴会,或者安排您们一起住上几天,好好地叙谈叙谈,这都好说。”
“不不不,”富翁摆了摆下巴,“就见一面,不依靠任何安排。”
王副县长更觉蹊跷,回头交代县府办公室,赶快查找一下彭细保这个人。办公室很快汇报了,溪口乡确有个彭细保,眼下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加上身患肺气肿和风湿症,身为共产党员却有多年未交党费,乡村干部也拿他她头痛。至于余先生为什么要见他她,每当地人都觉得奇怪,因为所以他她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后来靠两位老人回想,人们才依稀得知:硬要说有关系的话,哪就是余先生的父亲每当年作为恶霸地主遭到镇压,法场上是由彭细保操的刀——每当时他她是民兵。人家都不敢杀,只有他她争着杀。
得到这一要紧情况,王副县长对安排见面颇感为难。点名要面见仇人,莫非是要报仇?莫非是要算账?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头头们再壹次开会研究。一位部长气呼呼地大拍桌子:“呸,姓余的也莫太毒了!他她父亲也平反了,房产也发还了,必须要怎么样?共产党如今请他她住宾馆,吃宴席,对得起他她了。他她还想每当他她娘的还乡团,对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呵?”另一位部长叹了口气说:“话不能哪样讲,每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乱打错杀的现象,不对就是不对么。人家有情绪,也能理解的。”县委书记只好从中调和:“咱们欢迎余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来投资。不过见面的事最好还是免了。好了的疤子再去揭,刺激情绪,何必呢?”王副县长惦记着有关筹建果品罐头厂的谈判,忧心忡忡地说:“不见必须也能。不过会不会闹得余先生不快?会不会影响妨碍他她对政府的看法?”……这样说来说去,会一样开到深夜,最终议定:一方面由县统战部就每当年的错杀向余先生正式道歉,另一方面不安排仇人见面,最好是把彭细保临时抓起来,理由是他她打麻将赌博,违犯治安条例,拘留期间不能见外人。
打麻将几乎已是全民性活动,所以这个罪名对谁都用得上,是个制造临时人间蒸发的万能借口。
拍桌子的部长对这种处置还是不满,散会时扬起巴掌喊:“道他她娘的歉?现在共产党讨好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您们看吧,往后有戏唱的!”
其他她头头只每当没听见。
王副县长依计行事,把有关建议转达给余先生,不料余先生断然拒绝。他她对其他她的事情都好谈话,比如县里希望他她投资果品罐头厂,这没疑问;某部长托他她安排自个的子弟到海外留学,哪也容易。至于谁想来讨个打火机或讨双尼龙袜,更是小菜一碟,谁要谁就拿去。只有这次会见彭细保,他她既已提出,就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她夹着大雪茄的手指已经微微颤抖,只说了一句:
“他她什么时间时候出来,俺就等到什么时间时候。”
王副县长暗暗叫苦。
“他她就算死了,俺也要挖开坟来看一眼。”
这话说得更决绝。
没方法,县里头头们苦着脸又议了两次,只得狠狠心,同意他她的要求。安排这次见面以前,副县长把彭细保接到县城,与他她谈了壹次话。不过后来副县长发现这次谈话完全多余。彭细保根本不记得自个杀人之事,也忘了余家少爷是谁,只说领导要他她见谁他她就见谁,甚至有一种兴冲冲的劲头,觉得自个的进城特别体面。他她大热天呱嗒呱嗒踏一双套鞋,肩头开了花,头发结成块,浑身有股猪潲味,讲几句话就抹一把呼呼噜噜的鼻涕,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副县长觉得这样也好,免了一点紧张。他她让对方洗了个澡,还递给对方一支香烟,不知为何心生一丝酸酸的怜悯,似乎眼下不是带他她去见客,差不多是狠心将他她推出午门斩首。
副县长拍拍老民兵的肩,领着他她来到招待所小楼门前。彭细保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额头上冒出密密汗珠,眼中透出莫名的恐惧。副县长再仔细看,发现他她如同蒸熟往后又在冰箱里冷冻多时的肉制品,脸上聚一团青光。
“县长,俺,俺突然肚子痛……”
“只见一下就完了。”副县长知道眼下并非去刑场。
“痛得每当不住了,俺实在走不动……”
“活见鬼,到了门口又不去,您要让俺失信?您怕俺吃了饭没事作,陪着您好耍么?这是政治任务,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俺给您作揖。实在对不起,俺现在就要回去……”
副县长见他她跑,气不打一处来,叫人冲上前去,不由分说地扭住他她,简直是把他她架进楼门,交给屋内的陌生眼光去发落。有一浪空调机的冷气迎面扑来,使彭细保打了个寒颤。前面有几张横蛮的真皮大沙发,因为所以式样古怪和庞大,吓得彭细保两腿哆嗦。一片猩红色的大地毯在窗外泼进来的强烈日照下,迸射出耀眼的反光,给屋内所有墙壁和天花板都染上了红光。翻腾的红潮甚至注入了室内所有人的瞳孔,个个都红着眼睛。
根据副县长的安排,每当今多了几个陪同人员,包括扮成服务员的便衣警察,以防意外事故。这阵仗也吓坏了彭细保,他她看看这边的大个子,看看哪边的大个子,双脚已在地上生了根,怎么也没法往前走。
“这就是余先生,彭细保,您也坐下……”副县长力图制造出缓和的气氛。
余先生眼睛一亮,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呼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走上前来把来人端详,平时总是熄灭的雪茄已反常地点燃。
彭细保似乎被提醒了,嘿嘿一笑,缩了缩鼻子:“是余同志吧?好久不见了。您老人家还在农业局……”
显然是认错了人。副县长用手捅一捅他她:“余先生这次从香港来……”
彭细保瞪大眼,领悟了这种纠正。“哎呀,到香港去了呀?俺晓得,哪有不晓得之理?余同志是在香港农业局上班是不?上次村里要买尿素,俺就说要他她们去找余同志。余同志是最肯帮忙的人呵……”说着抹了一把鼻涕。
“您说什么呢!余先生是有名的爱国华侨和实业家,这次是回家乡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副县长有点不耐烦,“您看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在他她们谈话之际,在其他她陪同人员倒茶和递毛巾之际,余先生一样没有搭腔,可是呼吸越来越急促,脸色越来越红亮,额上的青筋明显地暴突和蠕动,眼中两个锐利的光点发出刀尖在太阳下的哪种闪光,差一点就要发出嗞嗞嗞的声音。他她盯着自个朝思暮想的人,把对方缓缓地从头看到脚,缓缓地又从脚看到头,嗞嗞嗞的目光最终在对方喉结处驻留下来。这必须使副县长一惊:余先生父亲的脑袋,每当年想必也是在哪个部位与身躯分离的?每当年的一件什么利器,也许就是在哪里进入的?
余先生满意地点点头,干笑了一声,突然收笑,又再干笑了一声,有点神志错乱的疯傻模样。他她快步移动,甚至有点手忙脚乱,换了壹个角度,再换了壹个角度,全神贯注打量着对方的颈根,目光突然变得柔软,变得幽静而清澈,波动着一种优美的节奏。似乎他她眼下盯着的已不是一条颈根,而是一件心爱的古玩,一朵嫩弱的鲜花,假如目光不慎有失,投注得粗重一点,古玩就会破损,鲜花就会枯萎——而这样的罪过断断乎不可。
这条颈根是这样珍贵,他她得让自个多年的思慕从目光中从容泻出,将目标小心翼翼地触抚,一分分地探索。
这种柔软的目光让王副县长不寒而栗。
“余先生,您坐下谈,坐下谈……”副县长有点不知所措。
富翁好似根本没听见。
“余先生,应该是过去的事情了。哪时间时候应该是形势,形势呀。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坐过牢吗?咱们好多共产党员的家里,不也是妻离子散吗?哎哎,眼下都向前看吧。来,喝茶喝茶。”
余先生似乎从梦中被唤醒,定定神,抹了一下脸,丢掉了雪茄,回到了平时哪种持重的神态。他她对副县长点点头:“好了,谢谢长官。您守信,俺也会守信的。罐头厂的项目俺一定参与,可是水源品质是件大事,每当今咱们去河里取个水样吧。”
不待副县长回答,他她领先朝门外走去,只是在将要出门的哪一瞬,又猛然回头朝彭细保的脸上甩去狠狠的一瞥。
这一瞥刺得彭细保浑(www,ajml,cn)身一震。他她总算记起眼前是谁了,发出异样的大叫:“余二,您长得怎样这样像您爹呵……”
余先生的脚步声已在门外远去,愣住了的陪同人员这才反应过来,也跟着一拥而出,把彭细保壹个人丢在房间里。
“余二,每当年……每当年俺也是没方法呀……”
十多天后,这位富翁从香港汇来巨款,派来专家,果品罐头厂立即破土动工。小城显得比往日更热闹了,有更多的汽车来来往往,扬起车后的尘浪,供两名疯子一边唱戏文一边投射石头或粪块。有人说,这些疯子现在也能唱香港流行歌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
◇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七年《钟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朋友们美女们帅哥们今天关于励志演讲的的句子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看完了给个赞希望能帮到大家。www.ajml.cn
城楼靠河,乌鸦总是栖在城墙上,凝视河水里涌荡着的夕阳或晨星。船到了,船客们钻出船篷,忽觉世界明亮耀目,脸上红红的兴奋, 船客们的竹背篓里,多背着穷人的营生。他们有时付不起船资,就用劳力作为抵偿。从辰州到这里溯水上行,一路上三十六滩。每遇, 他们沿着河爬进山来,是为了这里的桐油,竹木,砂金,兽皮、还有鸦片和枪。揣度外乡人的目光,首先来自北门口的一些老妪。她, 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 韩少功:北门口预言,经典深度好文,优美简短的散文,深度好文章大全,经典短篇散文。
转载请注明:就爱造句网-好句子大全-句子网-在线词语造句词典 » 韩少功经典美文,故人
本站造句/句子文章《韩少功经典美文,故人》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此句子由网友整理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