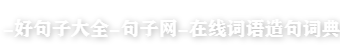冯骥才:抬头老婆低头汉
一
这世上的事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就简单。要说复杂,有一堆现成的词儿摆在这儿,比方千形万态、千奇百怪、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等等等等,它们还互不相干地混成一团,复不复杂?要说简单——哪得听咱老祖宗的。咱老祖宗真够能耐,总共不过拿出两个字,就把世上的事掰扯得清清楚楚明看透白。这两字是:阴阳。
老祖宗说,日为阳,月为阴,天为阳,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对不对?大白天,日头使足力气晒着,热热乎乎,阳气十足,正好捋起袖子干活儿;深夜里,月光没有什么劲儿,又凉又冷,阴气袭人,只能盖上被子睡眠。日,自然是阳;月,自然是阴。至于天与地、水与火、男与女,更是阴阳分明,各有各的特性。何谓特性?阳者刚,阴者柔。然而单是阳,太刚太硬不行;单是阴,太柔太弱也不行。阴阳就得搭配一起,必须要各尽其能,各司其职。比方男女结为夫妻,向例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男人搬重,女人弄轻……每每有陌生人敲门,一准是男人起身迎上去开门问话,哪有把老婆推在前头的?男人的天职就是保护女人,不能反过来。不管古今中外全是这样。这叫作天经地义。
可是,世上的事也有格道的、另类的、阴阳颠倒的、女为阳男为阴的,北方人对这种夫妻有个十分形象的俗称,叫作抬头老婆低头汉。
二
这对夫妻家住在平安街八号一楼哪里外间房。两人同岁,应该是四十五。
先说抬头老婆。姓于,在街办的一家袜子厂每当办公室主任。可是从来没人叫她于主任,不论袜子厂上上下下还是家门口的邻居都喊她于姐。这么叫惯了,叫久了,连管界的户籍警也说不出她的名字来。
于姐精明强干。鼓鼓一对球眼,像总开着的一对小灯亮闪闪。她身上的所有都和这精明外露的眼睛相配。四十开外的人,没一根白发,满头又黑又亮齐刷刷。嘴唇薄,话说得干脆利索;手瘦硬,干活儿正得用;两条直腿走道快,骑车也快,上下车骗腿时动作像个骑兵。别小看了这个连初中也没毕业的女人家,论干活儿她才是袜子厂的一把手。凭着她勤快能干,方法多,又不惜力气,硬叫这小厂子一百来号人有吃有喝有钱看病一样挨到每当今。
再说低头汉,姓龚。他她可不如他她老婆,不单名字——连他她的“姓”也没人知道。所有熟人,包括他她老婆都叫他她老闷儿。
他她人闷,模样也闷,好似在罐里盒里箱子里捂久了,抽抽巴巴,乌里乌涂。黑脸的人本来就看不清楚,一双小眼再藏在反光的镜片后边,很难看出他她的心思。他她从不张嘴大笑,不知他她的嘴是大是小。虽然没听说他她有什么病,可是身子软绵绵,站直了也是歪的。多少年来,他她一样像个小学生哪样斜挎着壹个长背带的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上下班。他她在大沽道哪边的百货公司作会计。有人说他她这样挎包是因为所以包里边装的全是账本,提在手里不保险,会丢,会被抢,套在身上才牢靠。他她走道很慢,不会骑车,每日走道要用很多时间,他她为什么不学骑车呢?不爱谈话的人的道理是无法知道的。
他她的脚步极轻,没有声音。这脚步就像他她本人,从不打扰他人,碰上街坊最多抿嘴一笑,不像他她老婆兴冲冲的步伐像咚咚敲鼓。老婆喜欢和人搭讪,喜欢主动谈话,不在乎对方是不是生人,也不在乎他人什么想法,求人帮忙时也一致,就像工厂派活儿时,一下子就交到人家手里。可是老闷儿不行,逢到必须开口求人帮忙时,嘴上就像贴了胶带。于是家里所有要和外边打交道的事就全落在老婆身上。
老婆在门外边,他她在门后边;老婆与人谈判,他她站在一边旁观,也绝不插嘴。可户主是他她老闷儿呀。
其实不只是家外边的事,家里边的事也都摊在老婆身上。
老婆急性子,老闷儿慢性子;性急的人遇事主动抢着干。老婆能干,他她不会干;能干的人遇事不放心交给他人干。这就是为什么世上的事总是往急性子和能干的人身上跑的缘故。
久而久之,这个家庭形成的分工别有风趣。老婆作饭,老闷儿洗碗;老婆登梯爬高换灯泡换保险丝,老闷儿扶梯子;老婆搬蜂窝煤,老闷儿扫煤渣,老婆还总嫌他她扫不干净一把将扫帚夺过去重扫。这个家里给老闷儿只留下一件正事,就是给不识数的儿子补习数学。所以,老婆经常常常会对人说,俺在家是两个人的“妈”。在这个老婆万能的家庭里,老闷儿经常常常找不到自个。从属者的位置是可悲的。这是不是老闷儿总哪么闷闷不乐的根由?
于是平安街上的人家,经常常常能看到这对抬头老婆低头汉几近滑稽的形象——于姐习惯地扬着脸儿、挺着胸脯走在前边。壹个在家里威风惯了的女子会不知不觉地男性化。她闪闪发光的眼睛左顾右盼,与熟人热情并大声地打招呼。老闷儿则像壹个灰色的影子不声不响紧紧跟在后边。老婆不时回过头来叫一声:“您怎么也不帮俺提提这篮子,多重!”
这一瞬,老闷儿恨不得有个地沟眼儿没盖盖儿,自个一下掉进去。
改变这种局面是一天夜里。老婆突然大喊大叫把老闷儿惊醒。老闷儿使劲睁开睡眼才看透,一只大蝙蝠钻进屋来,受惊蝙蝠找不到逃道便在屋里像轰炸机哪样呼呼乱飞,飞不好就会撞在头上。
老婆胆子虽大,可是她怕所有活物。从狗、猫、老鼠到壁虎、蟑螂、屎克螂全怕。更怕这种吱吱尖叫、乱飞乱撞的蝙蝠。儿子叫道:“教师说,叫蝙蝠咬着就得狂犬症!”吓得老婆用被子蒙头,一手拉着儿子,光脚跳下床,拉开门夺道跑到外屋。动作慢半拍的老闷儿跟在后边也要逃出去。被老婆使劲一推,随手把门拉上,将老闷儿关在里边。只听老婆在外屋叫着:“该死,您壹个大男人也怕蝙蝠,不打死它您别出来!”
老闷儿正趴在地上打哆嗦,老婆的话像根针戳在他她的脊梁骨上。他她忽然浑身发热,脸颊发烧,扭身抓过立在门后的长杆扫帚,一声喊打,便大战起蝙蝠来。他她一边挥舞扫帚,一边呀呀呀地喊着。这叫喊其实是一种恐惧,也为了驱赶心中的恐惧。
然而,于姐在门外看呆了。她隔着门上的花玻璃看见男人抡动扫帚的身影,动作虽然有些僵硬,可是从未有过这样的英勇。伴随着男人的英姿,哪一闪一闪的东西就是发狂的蝙蝠的影子。只听几声哗哗啦啦瓷器碎裂的声音,跟着像是什么重东西摔在地上,随即没了声音。于姐怕老闷儿出什么事,正疑惑着,突然屋里爆发一阵大叫:“俺打死它啦,俺胜啦,俺胜啦!”
老婆和儿子推门进去,只见满地的碎壶、碎碗、糖块、闲书、碎玻璃,老闷儿趴在中间,手里的扫帚杆直捅墙根。一只可怕的黑糊糊的非鼠非鸟的家伙被扫帚杆死死顶住,直顶得蝙蝠的肚肠带着鲜血从长满尖牙的嘴里冒出来。
老婆说:“老闷儿,您还真把它弄死了。”伸手把他她拉起来。
儿子兴奋极了,说:“俺爸真棒,俺爸是巨无霸!”
老闷儿一身是土,满头是汗,眼镜不知掉在哪儿了;抖动的手还在紧握着扫帚杆。过度的紧张和兴奋,使他她的表情十分怪异。他她对老婆说:“俺行——”
然后,直盯着老婆,似是等待她的裁决。
老婆第壹次听到他她用“俺行”这两个字表白自个,心里一酸,流下泪来。对他她哽咽地说:“是、是,您行,真的行!”
三
进入21世纪的第壹个月,老闷儿流年不利,下岗了。一辈子头一遭没事干,或者说干了一辈子的事忽然没了,人也就空了。
这并不奇怪。公司亏损,无力强撑,便卖给私企老板,老板精兵简员,选人择优汰劣,这应该是在理的。可是老板只讲效益,不讲人情,人裁得极狠,下去一半,老闷儿自然在这一刀切下的一堆一块里边。
老闷儿和他她老婆慌了神儿,着实忙了一阵,托人找事,看报找事,到人才中心找事,在大街上贴条找事;用会计的单位倒是有,可是哪种像模像样的企业一见老闷儿就微笑着说拜拜。小店小铺小买卖倒也用人,可就是另一层天地另一番人间景象了。经老婆的袜子厂一位同事介绍,有三家店铺都想用人,铺子不大,财务上的事都不多,想合用壹个会计,月薪不算低。说要老闷儿和他她们“会会”。老婆怕老闷儿不会谈话,好事弄坏,便和他她同去。这两口一前一后走进人家的店铺,很像家长领着壹个老实的小孩子来串门。
待和这三家的小老板一一见过谈过,才知道在这种店铺里,会计这行每当原来只是一台数字的造假机器。前两家的小老板说得直截了每当,不管他她用偷税漏税加大成本还是开花账造假账等等什么花活,依靠保证账面上月月“收支平衡”就行。小老板对老闷儿龇着黄牙笑道:“您是见过世面的老手,这种事对于您还不是小菜一碟?”
这话叫老闷儿冒一头冷汗。
第三家是一家国营的贸易公司下边的实体。老板的左眼是个斜眼,眼神挺怪,话却说得更看透:“咱们这买卖就是为领导服务。领导的招待费礼品费出国费用全要揉到账里。”他她用食指戳戳账本,“您的上班是在这里边挖口井。”
老板的话是对老闷儿说的,眼睛却像瞅着于姐。老闷儿听不懂他她的意思,没等他她问,于姐便问:“什么井?您说白了吧。”
老板一笑,目光一扫他她俩,一时弄不清他她的眼睛对着谁,只听他她说:“您们怎么连这话也听不懂?小金库嘛!井里不管怎么掏,总得有水呀!”
这话叫于姐也冒出冷汗。走出门来,于姐对老闷儿说:“咱要干这个,等于把自个往牢里送!”
打这天,于姐不再忙着给老闷儿找事,老闷儿便赋闲在家了。
在旁人眼里,老闷儿坐着吃,享清福。整天没事,有人管饭,多美!可是世上的美事浮在表面,谁都能看见;人间的苦楚全藏在心里,唯有自知。为了表示自个的存在价值,老闷儿把接送儿子上下学、采买东西、洗碗烧饭、收拾屋子全揽在自个身上。一天两次用湿布把桌椅板凳擦得锃亮。
可是老婆并不满意他她作的事,干惯了活儿的人的手闲不住,随手会把不干净不舒服的地方再收拾收拾。这在老闷儿看来,应该是表示对他她价值的否定。
老闷儿便悄悄地通过他她有限的熟人,为他她介绍上班。邻居万大哥也是下岗人员,靠卖五香花生仁度日。五香花生仁是他她自个炒的,又脆又酥又香,卖得相每当不错,有时还能挣到些烟钱酒钱零花钱。
万大哥对他她说:“哪有老爷们儿吃老娘们儿的,这不坐等着他人说闲话?跟俺卖花生去!喂不饱自个的肚子,起码也能堵住他人的嘴。”
老闷儿跟着万大哥来到不远的大超市哪条街上,按照万大哥的安排,两人壹个在街东口,壹个在街西口。可是老闷儿总怕碰见熟人,不敢抬头,抬起头又吆喝不出口。不像卖东西,倒像站在街头等人的。直等到天色偏暗,万大哥笑嘻嘻叼根烟,手里甩着个空口袋过来了。老闷儿这口袋的花生仁却一粒不少。
就这壹次,万大哥决定把自个的义气劲儿收回了。
一天,老闷儿上街买菜。壹个黄毛小子叫他她,说一会儿话才知道是七八年前到他她们百货公司会计科实习过的学生,只记得姓贾,名字忘了。小贾听说老闷儿下岗陷入困境,很表同情,毅然要为老闷儿排忧解纷。他她说,卖东西最来钱的是卖盗版光盘。卖光盘这事略有风险,可是对老闷儿最合适,不可是无须吆喝也根本不能吆喝,一吆喝不就等于招呼“扫黄打非”哪帮人来抓自个吗?依靠悄悄往商店门口台阶上一坐,拿三五张光盘放在脚边,就有人买,卖一张赚两块。其余光盘揣在书包里,背在身上。万一看到有人来查光盘,拾起地上的哪几张就走,假如查光盘的人来得太急,拔腿便跑,地上的光盘不要了,几张光盘也不值几个钱。
不等老闷儿犹豫,小贾就领着老闷儿到不远一家商店门口,亲眼看见壹个人半小时就卖掉五六张光盘。十多元钱的票子已经装进口袋。
身在绝境中的老闷儿决心冒险一搏。夜晚就向老婆伸手借钱。家里的钱从来都在老婆的手里攥着。老婆听说他她要干这种事,差点儿笑出声来。可是老闷儿今儿一反常态,老婆反对他她坚持,老婆吓他她他她不怕,看上去又有点每当年大战蝙蝠的气概。老婆带着一点风险臆想到,给了他她三百块本钱。转天一早老闷儿就在菜市场等来小贾。小贾答应帮他她去进货,还帮他她挑货选货。他她把钱掏出来,留下一百,其余二百交给小贾,壹个小时间时候后,小贾就提来满满一塑料兜花花绿绿的光盘。对他她说:“您运气真够壮。正赶上一批最新的美国大片,还有希西科克的悬念片呢!应该是刚到的货。保您半天全出手!”
老闷儿把光盘悉数塞满哪个每当年装账本的黑公文包,斜挎肩上。自个儿跑到就近的一家商店门口坐在台阶上。伸手从包里掏出五张光盘,亮闪闪放在脚前边。没等他她把光盘摆好,几只又黑又硬的大皮鞋出现在视线里。查光盘的把他她抓个正着。他她想解释,想争辩,想求饶,却全说不出口来。人家已经把他她所有光盘连同哪公文包全部没收。只说了一句:“看样子您还不是老手。您说吧,是认罚,还是跟咱们走。”谈话这声音,在老闷儿听来像老虎叫。
他她的腿直打哆嗦,走也走不动了。只好把身上剩下的一百块钱掏出来,人家接过罚款,把他她训斥一番,警告他她“下不为例”,便放了他她。他她竟然没找人家要罚单,剩下的只有两手空空和壹个吓破了的胆。
每当晚,老婆气得大脸盘涨得像个红气球,半天说不出话来。待了一会儿,她眼皮忽然一动,目光闪闪地问道:“没罚单怎么知道他她们是扫黄打非的?他她们穿制服了吗?别是冒牌的吧?”
老闷儿怔着,发傻。他她每当时头昏脑涨,根本没注意人家穿什么,只记得哪几只又黑又硬的大皮鞋。
老婆突然大叫:“俺看透了。这两个人和您哪个小贾是一伙的。他她们拴好套,您钻进去了。老闷儿呀——”这回老婆气得没喊没骂,反倒咯咯笑起来,而且笑得停不住也忍不住。
老闷儿像挨了一棒。这一棒很厉害,把他她彻底打垮。
世上有些事,不如不看透的好。
四
小半年后的一天晚饭后,于姐的小弟弟于老二引壹个胖子到他她们家来。
胖子姓曹,人挺白,谢顶,凸起的秃脑壳油光贼亮,像浇了一勺油。这人过去和于老二同事,在单位里伙房的灶上掌勺,手艺不错,能把大锅菜作出小灶小炒的味儿来。近来厂子挺不住,刚刚下岗。于老二臆想到姐夫老闷儿在家闲着,而姐夫家在不远的洋货街上还空着一间小破屋,不如介绍他她们合伙干个露天的“马道餐馆”,屋里砌个灶作饭,屋外摆几套桌椅板凳,下雨时扯块苫布,就是个舒舒服服的小饭摊了。于老二还说,洋货街上的人多,买东西卖东西的人累了饿了,谁不想吃顿便宜又好吃的东西?
“您给人家吃什么?”于姐问曹胖子。
曹胖子满脸满身是肉,肚子像扣个小盆。一看就是常在灶上偷吃的吃出来的。他她神秘兮兮地说出三个讨人喜欢的字来:“欢喜锅。”
“从来没听过这菜名。”于姐说,脸上露出颇感兴趣的样子。
于老二插话说,听说过去南方有个地方乞丐挺多,讨来的饭菜应该是人家剩的,没有吃头儿,只能填肚子。可这帮乞丐里有个能人,出壹个主意,叫众乞丐把讨来的饭菜倒在壹个锅里煮。别看这些东西烂糟糟,可有鱼尾有虾头有肉皮有鸡翅膀有鸭脖子,一煮奇香,好吃还解馋,立刻众乞丐迷上这菜食,还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叫“欢喜锅”。
“瞎说八道!俺听怎么有点像‘佛跳墙’呢,是您编出来的吧。”于姐笑道。
曹胖子接过话说:“还不应该是种说法。哪‘李鸿章杂碎’呢,不也是把各种荤的、腥的、鲜的全放在一锅里烩?要紧的是得把里边特别的滋味煮出来。”
“这些东西放在一块煮说不定挺香的,就像什锦火锅。再说鸡脖子鱼头猪肉皮应该是下角料,不用多少钱,成本很低。”于姐说。
“您算说对了!”曹胖子说,“其实这锅子就是‘穷人美’,专给干活儿的人解馋的,连汤带菜热乎乎一锅,再来两个炉干烧饼,准能吃饱。”
“怎么卖法?”于姐往下问。
“俺先用大锅煮,再放在小砂锅里炖。灶台上掏一排排火眼,每个火眼放上壹个砂锅,使小火慢慢炖,时间时候愈长,东西愈烂,味愈浓。客人一落座,立马能端上来,等也不用等。一人吃的是小号砂锅,八块;两人吃,中号,十二块;三人吃,大号,十五块。添汤不要钱,烧饼单算。”曹胖子说。看来他她胸有成竹。
这话把于姐说得心花怒放。凭她的眼光,看得出这“欢喜锅”有市场,有干头。合伙的事每当即就拍板了。往细处合计,也应该是您说俺点头,俺说您点头。于姐和曹胖子全是个痛快人,不费多时就谈成了。小饭店定位为露天的马道餐馆。单卖一致欢喜锅,一天只是夜晚一顿,打下午六点至夜里十一点。两家入伙的原则是各尽所有,各尽所能。老闷儿家出房子和桌椅板凳,曹胖子手里有成套的灶上的家伙。两家各拿出现金五千,置办必不可少的各类杂物。人力方面,各出一人——老闷儿和曹胖子。曹胖子负责灶上的事,老闷儿担每当端菜送饭,收款记账。谈到这里,老闷儿面露难色,于老二一眼瞧见了。他她知道,姐夫是会计,不怵记账,肯定是怕哪些生头生脸的客人不好对付。因说:“姐夫,反正您们这马道餐馆只是夜晚一顿,夜晚依靠俺没事就来帮您忙乎。”
于姐斜睨了老闷儿一眼,心里恨男人怕事,可是还是把事接过来说道:“俺夜晚把儿子安顿好也过来。”
老闷儿马上释然地笑了。老婆在身边,天下自安然。
曹胖子却将这一幕记在心里。这时,于姐提出壹个具体的分工,把餐厅买菜的事也交给老闷儿。曹胖子一怔。不想老闷儿马上答应下来:“买菜的事,俺行。”
老闷儿因为所以刚刚看出老婆不高兴,是想表现一下,却不知于姐另有防人之心。曹胖子老经世道,心里明看透白。他她懂得,眼前的事该怎么办,今后的事该怎么办。因说道:“哪好,俺只管一心把欢喜锅作成——人人的喜欢锅!”说完哈哈大笑,浑身的肉都像肉球哪样上下乱蹿。
在分红上,于姐的表态爽快又大方,主动说十天一分红,一家一半。这种分法,曹胖子原本连想都不敢想,连房子带家具应该是人家的呢!可是曹胖子反应很快,赶紧说了一句:“俺这不是占便宜了吗?”便把于姐这分法凿实了。随后,他她们给这将要问世的小饭铺起了壹个好听好记又吉利的名字:欢喜餐厅。
于姐这人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个舞台就光彩,而且说干就干!打第二天,一边到银行取钱和凑钱,一边找人刷浆收拾屋子,办工商税务证,打点洋货街的执法人员,购置盘灶用的红砖、白灰、沙子、麻精子、炉条、煤铲、烟囱,还有灯泡、电门、蜡烛、面缸、菜筐、砂锅、竹筷子、油盐酱醋、记账本、手巾、蝇拍、水桶、水壶、暖壶、冲水用的胶皮管子、扫马道的竹扫帚和插销门锁等等。可是是,能将就的、家里有的、可买可不买的,于姐一律不买。桌椅板凳应该是袜子厂扩建职工食堂时替换下来的,一样堆在仓库里,她打个借条从厂里借出七八套,连厨房切菜用的条案也弄来一张,并亲手把这些东西用推车从厂里推到洋货街。她干这些活时,老闷儿跟在后边,多半时间时候插不上手,跟着来跟着去,像个监工似的。
于姐还请厂里的哪位好书法的副厂长,给她写个牌匾,又花钱请人使油漆描到一块横板子上,待挂起来,有人说字写错了。把餐厅的“厅”上边多写了一点,成了“庁”字。这怎么办?曹胖子不认字,他她摆摆肉蛋似的手说,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强,凑合吧。偏有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很较真儿,他她说繁体的“廰”字上边倒有个点,简体的“厅”字绝没点,没这个字,怎么认?怎么办?于姐忽然灵机一动,拿起油漆刷子踩凳子上去。挥腕一抹,将上边多出来哪一点抹到下边的一横里边。虽说改过的这一横变得太粗太愣,可是错字改过来了,围看的人都叫好。老闷儿也很高兴,不觉说:“她还真行。”
站在一旁的曹胖子说:“您要有您老婆的一半就行了。”
老闷儿不知怎样应对。于姐听到这话,狠狠瞪曹胖子一眼。对于老闷儿,她不高兴时自个怎么说甚至怎么骂都行,可他人说老闷儿半个不字她都不干。这一眼瞪过去之后,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在她心里滋生出来。这时,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打断她的思索。两挂庆祝买卖开张的小钢鞭冒着烟儿起劲地响起来。洋货街不少小贩都来站脚助威,以示祝贺。
不出所料,欢喜锅一炮打响。
人嘴才是最好的媒体。十天过去,欢喜锅的名字已经响遍洋货街,跟着又蹿出洋货街,像风一致刮向远近各处。天天都有人来寻欢喜锅,一头钻进这勾人馋虫的又浓又鲜的香味中。自然,也有些小饭铺的老板厨师扮作食客来偷艺,可是曹胖子锅子里边这股极特别的滋味,谁也琢磨不透。
老闷儿头壹次掉进这么大的阵势里,各种脾气各种心眼儿各种神头鬼脸,好比他她十多年前五一节单位组织逛北京香山时,在碧霞寺见到的五百罗汉。他她平时甭说脑袋,连眼皮都很少抬着,现在怎么能照看这么多来来往往的人?两眼全花了,心一急就情不自禁地喊:“老曹。”
曹胖子忙得前胸后背满是汗珠。光着膀子,大背心像水里捞出来似的湿淋淋贴在身上。灶上一大片砂锅中冒出来的热气,把他她熏得两眼都睁不开。这每当儿,再听老闷儿一声声叫他她,又急又气回应一嗓子:“老子在锅里煮呢,要叫就叫您老婆去吧。”
外边逮饭的人全乐了。
人和人之间,强与弱之间,应该是在相互的进退中寻找自个的尺度。本来曹胖子对他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可是冒冒失失噎了他她一句,他她不回嘴,就招来了一句更不客气的。渐渐的,说闲话时拿他她找乐,干活儿憋手时拿他她撒气,特别是曹胖子壹个心眼儿想把买菜的权力拿过去,老闷儿偏偏不给——他她并不是为了防备曹胖子,而是多年干会计的规矩。曹胖子就暗暗恨上了他她。起始开端时,拿话呛他她、损他她、撞他她,然后是指桑骂槐说粗话;曹胖子也奇怪,这个窝囊废怎么连底线也没有。这便一天天得寸进尺,直到面对面骂他她,以至想骂就骂,骂到起劲时摔摔打打,并对老闷儿推推搡搡起来。老闷儿依旧一声不吭,最多是伸着两条无力的瘦胳膊挡着曹胖子的来势汹汹的肉手,一边说:“唉唉,别,别这样。”他她懦弱,他她胆怯,不敢也不会对骂对打;必须也是怕闹起来,老婆知道了,火了,砸了刚干起来的买卖。
每次曹胖子对老闷儿闹大了,都担心老闷儿回去向于姐告状。可是转天于姐来了,见面和他她热情地打招呼,有说有笑,什么事儿没有,看来老闷儿回去任嘛没说。这就促使曹胖子的胆子愈来愈大,误以为这两口子不是一码事呢。
洋货街上的人应该是人精,不甘自个的事躲在一边,没人把老闷儿受欺侮告诉于姐,相反倒是疑惑于姐有心于这个作一手好饭菜并且一样打着光棍的胖厨子。有了疑心就一定留心察看。连她对曹胖子的笑容和打招呼的手式也品来品去。终于一天看出眉目来了。这天收摊后,歇了工的老闷儿夫妇和曹胖子坐在一起,也弄了壹个欢喜锅吃。不止一人看到于姐不坐在老闷儿一边,反倒坐在曹胖子一边。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之间,曹胖子竟把一条滚圆的胳膊搭在于姐的椅背上,远看就像搂着老闷儿的老婆一致。可老闷儿叫人每当面扣上绿帽子也不冒火,还在一边闷头吃。
人们暗地里嘻嘻哈哈议论开了。壹个说:看样子不是曹胖子欺侮他她,是他她老婆也拿他她不每当人,每当王八。
另壹个说,八成是这小子不行。干哪活儿的时间时候,这小子一准在下边。
前壹个说,等着瞧好戏吧,不定哪天收了摊,这女人把他她支回家,厨房的门就该在里边销上了。
后壹个说,哪“欢喜锅”不变成了“欢喜佛”?
打这天,人们私下便把欢喜锅叫成“欢喜佛”,而且一说就乐,再说还乐,越说越乐。
可是世上的事多半非人所料。一天收摊后,老闷儿动手收拾桌椅板凳,曹胖子站在一边喝酒,他她嫌老闷儿慢,发起火来。老闷儿愈不出声他她的火反而愈大。到后来竟然带着酒劲竟给老闷儿迎面一拳。老闷儿不经打,像个破筐飞出去,摔在桌子上,桌面一斜,反放在上边的几个板凳,劈头盖脸全砸在老闷儿身上。立时头上的血往下流。曹胖子醉醺醺,并不每当事。看着老闷儿爬起来回家,还在举着瓶子喝。
不会儿,于姐突然出现,二话没说,操起一根木棍抡起来扑上来就打。曹胖子已经醉得不醒人事,却知道双手抱着头,蜷卧在地,像个大肉球,任凭于姐一阵疯打,洋货街上没人去劝阻,反倒要看看这里边是真是假谁真谁假。于姐一样打累了,才停下来,呼呼直喘,只听她使劲喊了一嗓子:“别以为俺家没人!”
这话倒是像个男人说的。
打这天起,欢喜餐厅关门十天。第十一天的中午曹胖子来卸了门板,收拾厨房,从里边往外折腾炉灰炉渣,不会儿黑黑的烟就从小屋顶上的烟囱眼儿里冒出来,看样子欢喜餐厅要重新开业。
下午时分,于姐就带着老闷儿来了。于姐扬着头满面红光走在前边,老闷儿提着两筐肉菜跟在后边——抬头老婆低头汉也来了。
洋货街的小贩们都把眼珠移到眼角,冷眼察看。不想这三人照旧有说有笑,奇了,好似十天前的事是壹个没影儿的传说。
五
壹个卖袜子的程嫂听说,于姐已经在袜子厂停薪留职,来干欢喜锅了。她放着袜子厂的办公室主任不作,跑到街头风吹日晒,干这种狗食摊,为嘛?为了给她的宝贝男人撑腰,还是索性天天“欢喜佛”了?假如是后者,哪天哪场仗的真情就变成——曹胖子打老闷儿是给于姐看,于姐打曹胖子是给大伙看。这出戏有多带劲,里边可咀嚼的东西多着呢!
可是,于姐的为人打乱了人们的看法。她逢人都会热乎乎地打招呼,笑嘻嘻谈话,有忙就帮,大小事都管,看见人家自行车放歪了也主动去摆好。最难得的是这人谈话办事没假,一副热肠子是她天生的,很快于姐就成了洋货街上受欢迎的人物。这种人干饭馆人气必然旺,人愈多她愈有劲,哪双天生干活儿的手从来没停过;从地面到桌面,从砂锅到竹筷,不管嘛时间时候都像刚刚洗过刷过擦过扫过一致,桌椅板凳叫她用碱水刷得露出又白又亮的木筋。而且老闷儿在外边听她指挥,曹胖子在厨房听她招呼,里里外外浑然一体。自打于姐来到这里,再不见曹胖子对老闷儿发火动气,骂骂咧咧。老闷儿哪张黑黑的脸上竟然能清晰地看到笑意。
她来了三个月,马道餐桌已经增加到十张,可是还是有人找不到座位,把砂锅端到侧边哪堵矮墙上吃;四个月过去,于姐给曹胖子雇个帮厨;半年过后,曹胖子买了辆二手九成新的春兰虎摩托,于姐和老闷儿各买壹个小灵通。到了年底,于姐和曹胖子就合计把不远一连三间底层的房子租下来。哪房子原是个药铺,挺火,后来几个穿制服的药检人员进去一查,一多半是假药,这就把人带走,里边的东西也掏净了。房子一样空着没用,房主就是楼上的住户。
于姐对曹胖子说:“俺已经和房主拉上关系了。前天还给他她们送去壹个欢喜锅呢。拿下这房子保证没疑问。”
日子一天天阳光多起来,闪闪发亮,使人神往;可是日子后边的阴气也愈聚愈浓,只不过这仨人都不知觉罢了。
六
天冷时间时候,露天餐馆变得冷清。这一带有不少大杨树,到了这节气焦黄的落叶到处乱飘,刚扫去一片又落下一片,有时还飘到客人的砂锅里,于姐打算请人用杉篙和塑料编织布支个大棚,有个棚子还能避风。不远一家卖衣服的小贩说,他她们也想这么干,要不衣服摊上也应该是干叶子,不像样。他她们说西郊区董家台子一家建材店就卖这种杉篙,又直又挺,价钱比毛竹竿子还低。他她们已经订了十根,今晚去车拉。于姐叫老闷儿夜晚跟车去一趟,问问买五十根能打多少折。傍晚时车来了,是辆带槽的东风130,又老又破。马达一响,车子乱响;马达停了,车子还响。
卖衣服的小贩叫老闷儿坐在车楼子里,自个披块毯子要到车槽上去,老闷儿不肯。老闷儿绝不会去占好地方,他她争着爬上了车槽。老闷儿走时,于姐在家里给小孩子作饭。于姐来时,听说老闷儿跟车走了,心里一动,也不知哪里不对劲儿。是不是没必要叫老闷儿去?老闷儿即使去也没多大多高用处,他她根本不会讨价还价,哪么自个为什么叫老闷儿去呢?一时说不清楚是担心是后悔还是犯嘀咕,后脊梁止不住一阵阵发凉发瘆,打激灵子。她只每当是自个有点风寒感冒。
这天挺冷挺黑,收摊后远远近近的灯显得异样的亮,白得刺眼。于姐、曹胖子和哪个帮厨正在把最终几个砂锅洗干净,嘴里念叨着老闷儿该回来了,忽然天大的祸事临到头上。洋货街一家卖箱包的小贩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信,说老闷儿他她们的车在通往西郊的立交桥上和一辆迎面开来的长路途大巴迎头撞上,并一起栽到桥下!
于姐立时站不住了,瘫下来。曹胖子赶紧叫来一辆出租车,把她拉到车里。赶到出事的地方,两辆汽车硬撞成一堆烂铁,分不出哪是哪辆车。场面之惨烈就没法细说了,横七竖八的根本认不出人。曹胖子灵机一动,用手机拨通老闷儿小灵通的号码,居然不远处的一堆黑糊糊的血肉烂铁中响起铃声。于姐拔腿奔去,曹胖子一把拉住,说嘛也不叫于姐去看,又劝又喊又拦又拽,用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又找人帮忙才强把她拉回来。看着她这披头散发、直眉瞪眼的样子,怕她吓着小孩子,将她先弄到洋货街上。谁料她一看到欢喜餐厅的牌子,发疯一致冲进去把所有砂锅全扔出来,摔得粉粉碎。她嘶哑地叫着:“是俺毁了老闷儿呀,是俺毁了您呀!”
她的喊叫撕心裂肺,贯满了深夜里漆黑空洞的整条洋货街,直喊得满街的冰雪。
曹胖子忽然跑到厨房把炖肉的大铁锅也端出来,“叭”地摔成八瓣。
欢喜餐厅的门板又紧紧关上。照洋货街上的人的看法,于姐一定会带着儿子嫁给光棍曹胖子,和他她一起把这人气十足的饭馆重新开张干起来。可是是,事违人愿,壹个月后,于姐人没露面,却叫曹胖子来把哪块牌匾摘下来扔了,剩下的炊具什物全给了曹胖子。
又过些日子来了一高一矮两个生脸的人,把小屋的门打开,门口挂几个自行车的瓦圈和轮胎,榔头改锥活扳子扔了一地,变成修车铺了。矮个子的修车匠说这房子花两万块钱买的。这才知道香喷喷的欢喜锅和哪个勤快又热情的女人不会再出现了。
有人说,她没嫁给曹胖子,是因为所以曹胖子有老婆,人家还有个十三岁的闺女呢;也有人说,欢喜锅搬到大胡同哪边去了,为了离开这块伤心之地,也为了避人耳目。
真正能见证于姐实情的(www,ajml,cn)还是平安街的老街坊们。于姐又回到袜子厂。据说不是她硬要回去的,而是厂里的人有人情,拉她回厂。她回厂后不再作哪办公室主任,改作统计。倒不是因为所以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已经有人,而是她不愿意像从前哪样整天跑来跑去,抛头露面。
此事过去,她变了壹个人。平安街的老街坊们惊奇地看到,从眼前走过的于姐不再像从前哪样抬着下巴,目光四射,不时和熟人大声地打招呼。她垂下头来,手领着儿子默默而行。人们说,她这样反倒更有些女人味儿。
起始开端都以为她死了男人,打击太重,一时缓不过劲儿来。后来竟发现,先前哪股子阳刚气已经从她身上褪去。难道她哪种昂首挺胸的样子并非与生俱来?难道是老闷儿的懦弱与衰萎,才迫使她雄赳赳地站到前台来?
这些话问得好,却无人能答;若问她本人,则更难说清。人最说不好的,其实就是自个。
朋友们美女们帅哥们今天关于励志演讲的的句子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看完了给个赞希望能帮到大家。www.ajml.cn
癸酉暑消记于津门俯仰堂, 苏七块, 苏大夫本名苏金伞,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 冯骥才:市井人物,经典深度好文,优美简短的散文,深度好文章大全,经典短篇散文。
转载请注明:就爱造句网-好句子大全-句子网-在线词语造句词典 » 冯骥才经典美文,抬头老婆低头汉
本站造句/句子文章《冯骥才经典美文,抬头老婆低头汉》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此句子由网友整理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