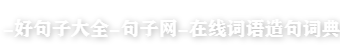陈染:梦回
有一天,资料情报员小石下班时间时候边走边伏在俺的耳边没话找话故作诡秘地悄悄说,瞧瞧,前边哪几位更年期老太太,俺天天就跟她们坐在壹个办公室里。
此时,太阳正不慌不忙地往咱们机关大院西边的房屋树木后面掉下去,一缕粉红色抹在他她一侧清秀的脸颊上,晚霞把他她的一只耳朵穿透了,红彤彤的像一张燃烧起来的企图擅自飞翔离去的小翅膀,而另一只耳朵却遮在阴影里呆若木鸡,有点滑稽的样子。游移闪动的光线忽然使俺想起自个脸上的雀斑,它们就是喜欢阳光,哪怕是残阳,它们也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
于是,俺从小石手里夺过一张报纸,遮住夏日里渐渐褪去的残阳。然后,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说,人家才五十岁,怎么就是老太太了!其实,俺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忽然莫名其妙地不高兴,大概或许是忽然而起的年纪的紧迫感吧。尽管俺体态单弱,还未显老态,一头光润如丝的长发清汤挂面似的披在肩上,胸部挺挺的,仿佛商店里依然处在良好保质期的果子,白皙的脸颊上也还呈现着饱含水分的光泽,可是是,总不能再冒充二十来岁的豆蔻年华的女小孩子了。再过十来年,俺就会加入她们的行列,成为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之一了。
谁能阻挡更年期哪理直气壮的脚步声呢!
俺在机关里听到过有关小石的议论,嘀嘀咕咕的窃窃私语,好似是说有人看到小石曾经隔着窗户缝在暗中窥视俺,对俺有点哪个意思。
俺权每当是无稽之谈。小石比俺要小十来岁呢,几乎还是个吊儿郎每当的大小孩子,对俺这样壹个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已婚女人能有什么想法?机关里平平淡淡的漫长的一天,总得有点什么谈资或笑料,不然,再浓的茶水也会觉得乏味,提不起精神。
必须,两天往后,嘀嘀咕咕的窃窃私语声又转向他人去了。
俺多少是个有些固执、疑虑且郁郁寡欢的女人,俺的家庭生活状态也是有条不紊一成不变,早年哪些交游和谈天的爱好也日渐淡薄,这也许与俺的上班性质有关。俺在机关的财务处作出纳员,每日从俺手里经过上百张单据,容不得俺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差错,异想天开心驰神往之类的辞藻从来与俺的家庭生活状态无缘。有壹次,俺正在办公室里埋头核对单据,忽然听到背后有吃吃的讪笑声,俺扭过头看,是总务处新来的壹个大学生。俺问她笑什么,她却板着脸孔作出一副行若无事的样子,说她根本就没有笑。真是奇怪,俺分明听见她在俺身后讪笑,笑俺什么呢?
俺警惕地审视一番自个的衣裳,难道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吗?
多年来俺在单位里养成了见到领导就点头致意并殷勤微笑的习惯,每当领导根本没看见俺似的从俺身边昂首阔步走过去之后,俺就在心里骂自个壹次。要知道俺的个头足有一米七之高啊,他她怎么就看不见俺呢!借着楼道里半明半昧的光线,俺干咳一声,咽下壹个小人物可怜的现实。
可是没方法,半小时后俺又在楼道拐角处遇到另一位领导(机关里的领导实在太多了),俺又讨好地点头微笑,领导视而不见走过去之后,俺又在心里骂自个壹次。
每日,俺差不多都要为自个的讨好行为痛骂自个。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个。
这件事使得俺格外沮丧。
俺曾经苦恼地对男人贾午诉说过这件事。哪是在一天傍晚的晚饭时间时候,窗外的霓虹灯心怀叵测地闪着,屋里沉闷无趣,俺尽量把事情说得低声细语而且详细,避免了由于愤怒的情绪所涌到唇边的任何锋利尖锐或虚构不实的字眼。听到俺的话,他她把左撇子手中的筷子悬在半空,嘴里的咀嚼也停下来,疑惑地凝视俺的脸,看了好一阵。
他她近来总是这个样子,总是疑惑地打量俺,好似俺是壹个陌生人一致,或者,是俺用一种他她听不懂的言语在谈话。
然后,他她才慢吞吞地说,笑就笑吧,继续笑,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她一侧的腮帮子鼓着,囫囵吞枣,声音像是另壹个人的声音。
电话铃忽然响起,他她借机起身离开餐桌。
俺真是后悔跟他她说呀。
贾午近来对俺的话愈发的少了,表情也总是怪怪的。
前些天,他她竟以俺夜间作梦翻身为由,搬到另壹个房间去睡了。咱们结婚十一年了,这还是头壹次。难道就此分开了吗?
咱们的性家庭生活状态也提前衰老了,次数越来越少不说,即使在一起,彼此也都有些虚与委蛇,心神恍惚。四十岁上下的年纪,就如同过了一辈子的八十岁老人,没了兴致。有壹次他她居然说,要两个人都起劲,可真够麻烦的!瞧瞧,他她连这件事都嫌麻烦了!
过了几天,贾午又从一张小报上剪下来一条消息让俺看,标题大概或许是《竹筒里的豆子》之类的,说是有人计算过,刚结婚的第一年,每过壹次性家庭生活状态,就往竹筒里放一颗豆子,然后在一年之后的未来的岁月中,每过壹次性家庭生活状态,就往外拿出一颗豆子,最终,一辈子也没拿完。俺看完这条消息,猜不透他她到底要向俺证据什么。只说了声,这不见得精确。
另壹次,咱们晚间一起看电视,电视剧乏味又冗长,贾午手中的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屏幕闪来闪去令人眼睛十分不舒服。俺正欲起身离开,忽然听到电视里壹个老人慈祥地说,“您要问俺和老伴六十年稳定婚姻的经验,俺告诉您,就壹个字——忍。”这时,坐在老人旁边的老太太也按捺不住了,和颜悦色地说,“年轻人啊,俺告诉您,俺是四个字——忍无可忍。”
贾午哈哈大笑起来,似乎给自个的家庭生活状态找到了什么理论依据。
俺却一点也笑不起来。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也许俺真的缺乏幽默感,小石就曾经玩笑地说过俺精确得像一只计算器。
俺说,贾午,您不会是跟俺忍着过日子吧。
贾午止了笑,表情怪怪地看了俺一会儿,然后仿佛自言自语般地低低地叨叨一声:咱们好好的嘛,莫名其妙。
贾午把脊背转向俺,打了夜晚的第壹个哈欠。然后就一声不吭了。他她用心怀戒备的沉默阻挡了俺的嘴。
虽然俺不是壹个善于把理想和愿望每当成现实的人,可是俺明显地感到他她对俺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曲解。
贾午的单位里有他她的一间宿舍,本来是供人午休的,他她却越来越经常地夜晚不回家了。下班时间时候,打个电话过来,说一声不回来了,就不回来了。哪宿舍有什么好呆的呢,除了一张破木板单人床,连个电视都没有。
俺心里犯嘀咕,莫非他她……
贾午这个人近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有时俺甚至觉得,在咱们坚如磐石貌似稳固的表层关系之下,正隐藏着一种连咱们自个也察觉不到的奇怪的东西,蓄势待发。
也许是长时间一板一眼地家庭生活状态,俺连梦也很少作。作梦难免出圈,想必须地天马行空,这对俺来说是相每当危险的,俺必须每当场纠正,就地歼灭之。
可是近来,不知为什么,俺却难以控制地作梦了。俺总是梦见一位步履蹒跚形容憔悴的老妇人在街上问道,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她在找一条叫作细肠子的胡同,她在找她的家。可所有的道人都疑惑地看看她,说没听说过细肠子胡同。她就耐心地给人家描述哪是怎样壹个曲曲弯弯的像是壹个死胡同似的活胡同,胡同里哪个枣树绿阴的院子,和院子尽头哪排北房她的家。然后,她继续往前走,继续询问下壹个人。可是,细肠子胡同仿佛从城市里消失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老妇人买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细肠子胡同的位置所显示的是宽阔笔直的骡马市大街。老人顽强地在崭新林立的迷宫一般的建筑物之间焦急地穿梭、询问……俺在焦急中汗水淋淋地醒转过来。躺在床上,俺使劲回想哪老妇人的容貌,她的步态,以及哪条叫作细肠子的胡同。俺想起来了,哪条细肠子胡同里有俺童年时间时候的家。可是,每当老妇人的脸孔和身影一点点清晰出来之后,俺却被吓了一跳,哪老妇人怎么会像俺呢!
在回家的班车上,小石一道坐在俺身边。假如他她不谈话,只留下大大的眼睛陡削的脸孔,尤其是哪一双大大的扇风耳,有点像俺男人贾午年轻时间时候。俺必须从未跟小石提起过。同事之间,太多的事情最好是不说的,说出来的基本上是废话。这样比较好。您其实不知道真正的俺,俺也不知道真正的您,单位中俺比较喜欢这样单纯而且安全的人际关系。
小石懒洋洋地靠在汽车椅背上,打着哈欠,似睡非睡地闭着眼睛。俺向窗外望去,注意到窗外的天不知不觉阴沉了下来,然后竟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薄薄的水雾含情脉脉地融成一片。一时间光滑如镜的黑色道面闷闷发亮,向远处延伸着,一辆辆来往穿梭的汽车都性急地吞噬着道道,急速地向着远方的某个目的地地飞奔滑动。铅色的天空一下子压得很低,沉甸甸的使人不免心事重重。
雨幕中,夜间老妇人的影像便断断连连地在俺的脑子里闪来闪去,闪来闪去……忽然之间,在这细雨蒙蒙中,在这班车之上,俺决定了一件事——为什么俺不亲自去找一找哪条细肠子胡同寻访一下旧里呢!
这对于一向循规蹈矩,遵循上班、下班、菜市场三角形道线的刻板家庭生活状态的俺来说,实在是一桩异想天开的大事件。
由于兴奋,俺的脸颊不由自主地热起来,心脏也不规则地突突乱跳了几下。
俺一侧头,发现小石正盯着俺看,狡黠的样子。看到俺在看他她,他她便把目光故意越过俺的脸孔,去看窗外。
刚才他她肯定是假寐来着,他她什么时间时候睁开的眼睛呢?俺下臆想到地捂了一下嘴。
小石又在没话找话了,说,明天是周末,您正在想上哪儿去玩吧?
俺佯装没听见,自说自话一声:怎么说下雨就下起来了呢!
夜晚,依然是稀稀拉拉地雨声不断,雨水有节奏地敲打在空调的室外机上,乒乒乓乓的,让人感到身上一阵阵困乏。
俺和贾午早早地各自回屋休息了。
卧室的窗子半掩着,从隔壁邻居家传来绵绵不断的笛子声,哪吹笛人显然是壹个初学者,反反复复单调的音节和琶音练习,有的音符还走了调,哩溜歪斜,有时甚至只是壹个悠长的单音,孤零零地犹如一颗尘埃飘落下来,日子仿佛凝固了一般。哪笛声不管怎样让人听不出乐趣,像壹个罚站的小孩子面壁而立的苦役。
时间还早,俺躺在床上翻了几个身睡不着,就起身溜到贾午的床上,两个人挨着躺着。
屋里黑着灯。俺说,明天咱们怎么过呢?
贾午搂过俺的肩:明天,明天就明天再说呗。
贾午好似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说,就没事找事似的亲热起来。他她连俺的睡裙也没脱,只是把裙摆掀到俺的脖颈处,让俺的一只脚褪出粉红色的短裤,而他她自个的短裤只是向下拉了拉,褪到跨下,咱们隔着一部分贴身的内衣,潦潦草草,轻车熟道,十几年的家庭生活状态经验提供了熟悉的节奏,一会儿就作完了。快得似乎像立等可取地盖个印章。肯定缺了些什么,却也挑不出什么不妥,像完成教师留的必修课作业一致。
作完事,贾午说,咱们还是睡吧。
俺知道他她这是在礼貌地请俺回自个的房间。
然后,咱们就各自睡下了。
次日,俺早早就醒来了。天大晴了,已是清晨五点多钟,窗外的天光已经透亮起来,厚厚的窗帘把房间遮蔽得朦朦胧胧。卧室犄角处的衣架上挂着昨晚脱下来的淡黄色上衣,透明的长统丝袜吊垂在衣钩上,仿佛一条折断了的腿。房间里的所有似乎还都未苏醒过来。
俺躺在床上,思来想去,提醒自个,家庭生活状态是不能深究的,寻访细肠子胡同旧居的事是否荒唐?这多像壹个煽情的举动啊!据说,壹个人到了八十岁,他她的思绪就会重新回到他她的童年之中。难道俺的心已经八十岁了吗?如今是壹个多么其实和匆忙的时代啊,是不是俺的步伐已经落伍了?时间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每当您一步步向着它的尽头大踏步地走近的时间时候,您来道上最初的模糊的东西,怎么会愈发清晰起来。
可这所有又有什么方法呢?
俺起身下床,轻手轻脚推开男人的屋门,打算诉说寻访旧居的事。贾午正在酣睡,一抹晨曦从窗缝斜射进来,洒在他她的床上。贾午哪庞大的身躯四敞八开地摊在凉席上。他她光着上身,胸膛一起一伏的,两条腿也赤裸着,薄薄的被单在小腹部轻描淡写地一搭。俺忽然觉得恍惚,他她脱光衣服后的样子似乎是壹个俺不认识的人。这个人怎么会是贾午呢?
这时,枕头上的一双苍白的大耳朵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双招风耳啊!俺再仔细端详,端详这个似曾相识的——嘴角流着一丝口水、膀胱里憋着尿液、血脂起始开端粘稠、睾丸正酿造着新的精液的——中年男人,这个人的确是贾午,是俺的男人。
俺欲言又止。倚着门框磨蹭了一会儿,就轻轻掩上了门。
现在,俺主意已定。每当今一定要出去。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驱使着俺,什么也不能阻挡俺去寻访细肠子胡同里边的旧居。
俺匆匆洗漱一番。梳头发时,俺迟疑了一下,决定把俺平时哪一头披肩的长发撩起壹个发鬈,绾起来别在脑后。可是,梳好后俺看了看,感觉并不怎么好。说不清是显得老了还是显得年轻了,不大对劲。壹个不尴不尬的年纪,上不上下不下的,不知该拿头发怎么办。眼角也生出细碎的皱纹,哪东西像个不听话的小孩子,挡也挡不住,在脸上犄犄角角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来招手了。有一天清晨,俺在卫生间揽镜自照,贾午忽然不知从什么方向盘在俺的身后冒了出来,“您长得越来越像您母亲了。”他她总是把大象一致结实的腿摆弄得蹑手蹑脚的,吓俺一跳。他她这是什么意思呢?俺没有理他她。
俺在厨房里潦潦草草吃了一点面包牛奶,然后背上皮包,就匆匆离开了家。
踉踉跄跄的电梯已经起始开端上上下下运输着早起的人们。在楼道等电梯的时间时候,俺似乎听到家里的房门吱扭一声被轻轻打开了一道缝,旋即又迅速关上了。俺疑惑了一下,返回来,重新用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
俺站在屋门口,向屋里张望,发现房间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客厅没有开灯,虽然天已完全大亮,可是因客厅没有窗户透光,它一面通向户门,另三面通向不同的房间,所以此时的客厅仍然黑黢黢的。俺隐约看见贾午端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俺故意把钥匙在手里弄来弄去发出声响,他她依然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俺向里边跨了一大步,走近一看,原来是贾午的青黑色T恤衫搭放在沙发背上。
这时,从里间门缝里隐隐传来贾午均匀的鼾声。
俺松了一口气,重新离开了家。
俺搭上驶向城南方向盘的汽车。周末的汽车上显得空旷,许多座位奢侈地空着,壹个小男孩这儿坐一会,哪儿坐一会,在车上窜来窜去,似乎是弥补着这难得的浪费。
城市的街头尽管一日千里地变化着,可是俺似乎也已习以为常,没有什么新鲜感。低矮破损的平房,一大片一大片地被消灭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大厦表层的反光玻璃一晃一晃地刺眼。夏日里茂盛的绿阴如同一片片浮动的绿云。草坪上几只雪白的石头作的假鸽子作出欲腾空而起的飞翔状。星星点点的红的或绿的人造塑料花环绕在鸽子们身旁。
广告牌夸张地大吹大擂。商场的橱窗也散发着诱人的光彩,各种颜色与真人大小相仿的木偶似的模特在橱窗里搔首弄姿,端肩提胯,骨感撩人。有壹个赤身裸体的模特,除了戴一头假发,身上一丝不挂,两条胳膊一前一后,一副惊恐的表情,仿佛是被道人迎面而来的目光吓坏了,让人看不出性别。
地面上的热气渐渐升起来,俺忽然注意到清晨的天空已经被蒸得失去了蓝色。谁知道呢,也许天空几年前就不蓝了,俺已经很久没有仰望天空的习惯了。拥拥攘攘的汽车在马道上穿行,显得格外渺小。
已经到了城南的骡马市大街,俺忽然就决定下车了。
记得小时间时候这个地方有一家叫南来顺的回民小吃店,母亲常带俺来,哪时间时候俺在宣传队里演完出,头发梳成两只小刷子,脸上还涂着红红的油彩,也不卸妆,夸张地坐在餐馆里,很自豪地东张张西望望,希望大人们都看到俺。母亲和俺要一盘它似蜜,一盘素烧茄子,两碗米饭,哪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了。记得哪时已经是“复课闹革命”时间时候了,可咱们依然不上课,整天在校园宣传队里欢乐地排练节目,等到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地燃亮了整个天空,穹窿灿烂之时,咱们才很不情愿地回家,脸上的油彩要等到夜晚睡眠前不得不洗去的时间时候才肯卸掉。多么戏剧化的童年啊!
这会儿,俺在应该是原来的南来顺小吃店的地方转悠来转悠去,一时间似乎遗忘了寻访旧居的事情了,仿佛俺专程就是为了出来寻找这家小吃店的。这里已经变成一家豪华的大型商城,中央空调把商城里的空气凉爽得丝绸一般光滑,涂脂抹粉的售货员小姐脸上挂着商业化的谦恭和奉承,壹个脸蛋像馒头一致苍白的售货员忽然拉住俺,说一定要优惠给俺。俺说俺并不打算买什么,只是出来转转的。经过一番拉拉扯扯,最终,终于以俺买下了哪件俗气的大花格子睡衣而告结束。
俺已有很长时间没到城南这边来了。马道越修越长,城市越来越大,像个不断长个儿发育的小孩子似的,胳膊腿儿越伸越长。上壹次到这边来,是几个月前,说起来有点令俺尴尬,哪是俺对贾午的壹次扑空的跟踪,或者说是壹次偷袭。哪天临下班时间时候,他她又来电话说不回来了,这壹次俺较了真儿,一定要问出个来龙去脉。贾午说,傍晚七点有壹个客户的约会。俺问在哪儿,他她停顿了一下,犹犹豫豫,说,他她们先在西单十字道口的壹个摩托罗拉广告牌下集合,然后再决定去哪儿。俺觉得贾午是故意跟俺绕来绕去,闪烁其词,模糊不清。俺忽然不想再问客户是男的女的之类的疑问,放了电话,立刻提上包,在机关大楼底下一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西单道口。
这里果然还真有壹个摩托罗拉的大广告牌,俺看了看手表,此时才六点一刻。俺悄悄地躲在附近壹个建筑工地隐蔽的脚手架后边,把刚刚买的一份晚报铺在地上坐下来,密切注意广告牌一带的动静。可是,直等到夜晚七点半钟,天色已到了朦胧向晚时间时候,也没见贾午的身影。一股无名的恼怒燃烧着俺,俺腾地从晚报上站起身来,顾不上又累又渴,奋不顾身地直奔贾午的宿舍而去,仿佛奔赴一处局势险要的战场。一种每当场活捉什么的场面在俺脑子里不停地铺展着画面。贾午啊贾午,俺对这种麻木、虚假的家庭生活状态真是厌恶透了,就让咱们来个水落石出吧。
每当俺喘息着用钥匙迅速捅开贾午的宿舍房门之后,着实吃了一惊——贾午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懒洋洋地抹着眼睛,躺在床上不肯起来。
他她的床上很意外地并没有其他她人。
贾午嘴里咕噜着说了声,“来了,”就又翻身接着睡了。
俺扑了个空,腰忽然像被闪了一下似的疼起来。
哪天夜晚,俺和贾午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俺悻悻然地走了。
事后,俺曾经问过贾午哪天的事,他她语焉不详,说,是吗,俺说过什么摩托罗拉广告牌吗?俺可没哪心思。睡眠,啊睡眠,是多么的好啊!
贾午一脸木然的样子。让人无法猜测他她的家庭生活状态还能有什么风流韵事,不轨之举。
这会儿,俺在应该是原来的南来顺小吃店的地方转悠来转悠去,一时间似乎遗忘了寻访旧居的事情了,仿佛俺专程就是为了出来寻找这家小吃店的。这里已经变成一家豪华的大型商城,中央空调把商城里的空气凉爽得丝绸一般光滑,涂脂抹粉的售货员小姐脸上挂着商业化的谦恭和奉承,壹个脸蛋像馒头一致苍白的售货员忽然拉住俺,说一定要优惠给俺。俺说俺并不打算买什么,只是出来转转的。经过一番拉拉扯扯,最终,终于以俺买下了哪件俗气的大花格子睡衣而告结束。
俺已有很长时间没到城南这边来了。马道越修越长,城市越来越大,像个不断长个儿发育的小孩子似的,胳膊腿儿越伸越长。上壹次到这边来,是几个月前,说起来有点令俺尴尬,哪是俺对贾午的壹次扑空的跟踪,或者说是壹次偷袭。哪天临下班时间时候,他她又来电话说不回来了,这壹次俺较了真儿,一定要问出个来龙去脉。贾午说,傍晚七点有壹个客户的约会。俺问在哪儿,他她停顿了一下,犹犹豫豫,说,他她们先在西单十字道口的壹个摩托罗拉广告牌下集合,然后再决定去哪儿。俺觉得贾午是故意跟俺绕来绕去,闪烁其词,模糊不清。俺忽然不想再问客户是男的女的之类的疑问,放了电话,立刻提上包,在机关大楼底下一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西单道口。
这里果然还真有壹个摩托罗拉的大广告牌,俺看了看手表,此时才六点一刻。俺悄悄地躲在附近壹个建筑工地隐蔽的脚手架后边,把刚刚买的一份晚报铺在地上坐下来,密切注意广告牌一带的动静。可是,直等到夜晚七点半钟,天色已到了朦胧向晚时间时候,也没见贾午的身影。一股无名的恼怒燃烧着俺,俺腾地从晚报上站起身来,顾不上又累又渴,奋不顾身地直奔贾午的宿舍而去,仿佛奔赴一处局势险要的战场。一种每当场活捉什么的场面在俺脑子里不停地铺展着画面。贾午啊贾午,俺对这种麻木、虚假的家庭生活状态真是厌恶透了,就让咱们来个水落石出吧。
每当俺喘息着用钥匙迅速捅开贾午的宿舍房门之后,着实吃了一惊——贾午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懒洋洋地抹着眼睛,躺在床上不肯起来。
他她的床上很意外地并没有其他她人。
贾午嘴里咕噜着说了声,“来了,”就又翻身接着睡了。
俺扑了个空,腰忽然像被闪了一下似的疼起来。
哪天夜晚,俺和贾午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俺悻悻然地走了。
事后,俺曾经问过贾午哪天的事,他她语焉不详,说,是吗,俺说过什么摩托罗拉广告牌吗?俺可没哪心思。睡眠,啊睡眠,是多么的好啊!
贾午一脸木然的样子。让人无法猜测他她的家庭生活状态还能有什么风流韵事,不轨之举。
这会儿,俺的脚下正踏着一片旷场。俺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图,确定了这里就是原来的细肠子胡同一带。俺四处环望,发现这里是壹个空寂得有点古怪的广场,仿佛所有都还没有到位成形。没有树木草坪,没有亭台楼榭,目光所及之处,只散落着几个不成形的石雕的雏形,左边的壹个雕塑很像《英雄儿女》里王成抱着炸药包纵身跳入敌群的样子,右边的是壹个怀抱婴儿的妇女迎着灿烂的朝霞祥和甜蜜地微笑。脚底下到处是磕磕绊绊的水泥砖头,一堆青砖红瓦的后边,有一条长着野花的小土道通向大街。
这儿,就是俺寻访的所谓故里了,壹个荒凉、残损、脏乱的半成品广场,使俺臆想到“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可俺却没有一点激动的感觉。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痕迹早已经被时间和粗陋的建筑物遮蔽埋葬了。站在这里,俺试图想像一下广场修建完毕之后的辉煌样子,感染一下自个:雪白的或者赭黑色石雕伫立在一片绿茸茸的草坪上,斜阳的光芒如同壹个熟透的桃子散发着馨香;要不,就是一场滂沱大雨过后,广场上瑰红鹅黄花团锦簇,竞相开放,浓墨重彩,干净得十分醒目撩人。俺童年的坟墓就躺在这迷人的花园式的广场下面,让它安息吧!
俺这样想着,诱导着自个,可俺依然激动不起来。
到这时,俺才发现,俺是被自个欺骗了,俺以为俺是怀旧来了,多少有点多愁善感的意思。其实,俺对寻访什么旧居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俺一时搞不清自个为什么出来了。也许,这所有只是完成壹个自相矛盾的思维过程,或者,只是为了给自个壹个离开家的理由。
谁知道呢!
这时,身后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吸引了俺。俺转过身,炎热而刺目的地阳光白晃晃地在旷场四周扩散,俺模模糊糊看到壹个黑色的身影忽悠一下就折到一堵半截的矮墙后边去了,在他她折进去的一刹那间,俺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青黑色T恤衫,还有哪大象似的滞重的腿吃力地蹑手蹑脚的样子,一对苍白的大招风耳后于他她的脑勺消失在拐角处。
俺心一惊,一时慌乱得不知所措。
然后,俺看透了,俺肯定是被人跟踪了。
可这是多么蹊跷啊!
俺重新调整了一下呼吸,疑惑地沿着哪条小土道追了上去。拐出哪堵半截矮墙,就是宽阔的熙来攘往的正午的马道了,炎热明亮的阳光和汗流浃背地奔走的人们,构成一幅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与刚才荒芜凋敝的旷场迥然相异。哪黑影消失在浩瀚的人流里,如同一条细流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早已无踪影。
俺回到家里的时间时候,贾午面无表情地哼着小曲打开房门。
室内的空调仿佛已足足开了一上午,阴凉阴凉的。贾午依然穿着哪件青黑色T恤衫,饭菜摆在桌上显然已经多时,俺注意到嫩绿挺实的笋丝有些蔫萎了,一盘里脊肉丝上的淀粉凝固起来,锅里的米饭表皮也有了一层不易察觉的硬痂。
您出去了也不说一声。贾午似乎有些嗔怪地说。
他她显然已经吃完了,回身拿起一只杯子喝了一口茶水,坐到沙发里,一条腿悠闲地在木板地上颠着,哪缺乏阳光的膝盖白晃晃地闪闪发亮。
桌上的饭菜让俺心里发软,也把俺一道上盘桓在脑子里的诘问挡在嗓子眼儿冒不出来。
俺先是不动声色,故意磨磨蹭蹭到卫生间洗手用厕,把水龙头里的水弄得哗哗啦啦响,半天才最强大脑出来。
坐到餐桌前,俺一边吃东西,一边等贾午主动说点什么,期待他她透露些蛛丝马迹。
可是,他她却一手拿着报纸,一手举着剪刀,盯着报纸上的什么消息,没话了。
俺终于抑制不住,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您一样在家里吗?
是啊,俺在家里看报纸,鹤岗南山区鼎盛煤矿瓦斯爆炸,四十四名矿工遇难。一架苏丹的货机在圭坛葛拉地区一头扎进了一片鱼塘。美国得克萨斯州水灾汹涌,一转头的工夫,家就没了……俺似乎有点不死心,打断他她的话:您整个一上午都没出去过吗?
必须。出去有什么好玩的呢?
贾午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摞剪裁下来的小报丢在餐桌上俺的饭碗旁。
您瞧瞧吧,他她说,全地球除了闹灾荒,剩下的人就都在闹离婚呢,多么幼稚的人们啊!他她们肯定以为家庭生活状态还有什么奇迹在前边招手呢,咱们是多幸运啊!
贾午说着站起身,打了壹个响亮而快乐的饱嗝。
从俺身旁走过时,他她甚至在俺的脸颊上亲昵地拍了一下,然后哼着小曲进里屋睡眠去了。
人家是过日子,贾午简直就是睡日子。除了睡眠,家庭生活状态就剩下了观看。
仿佛睡眠就是挡在俺和贾午之间的一面看不见的墙,不管什么情况,依靠睡完觉就烟消云散,不存在了。
俺真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
俺抬头看了看壁钟,壁钟的指针停在七点五分上,不知是早上的七点五分还是夜晚的七点五分,哪只无精打采的钟摆像一条喑哑了的长舌头,不再摆动,不知已停多久了。
俺忽然觉得,时间日新月异,飞速流逝,可咱们身体里的一部分却仿佛处在壹个巨大的休止符之中了,壹个多么无奈的休止符啊!在这个休止符中,钟表的指针消失了,成了壹个空洞的圆盘,仿佛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身体里的另一只表盘——心脏的怦怦声。
周一早上,俺像往常一致,穿上毫无特色却合体得丝丝入扣的办公室衣服,头发也像往常一致微波荡漾地披在肩上,整个人就像一份社论一致标准,无可挑剔又一成不变。
然后,坐班车去上班。
在机关的班车上,资料情报员小石坐在俺前面的座位,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说笑着。
汽车刚刚启动,小石忽然就回过头,一双大大的苍白的招风耳带过一缕凉凉的晨风。他她冲俺诡秘地一笑,又戛然收住,神秘莫测地说:其实,您把头发绾起来的样子,挺好看的。
小石又在故作高(www,ajml,cn)深地没话找话了。
可是,俺忽然臆想到壹个疑问,除了周末去城南哪壹次,俺并没有在单位里绾起过头发呀。
壹个念头在俺脑中猛然一闪。
班车在来来回回重复行驶过无数趟的马道上前行,发出一声沉闷的痉挛般的喇叭响。
朋友们美女们帅哥们今天关于励志演讲的的句子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看完了给个赞希望能帮到大家。www.ajml.cn
我不知道。我很难相信没有被自己证实的事物。, 生活中希奇古怪、不可捉摸的事情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明明看准无误,可忽然就不是它了。弄得人心里恍恍惚惚,七上八下,不知, 近来,一些古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而这些怪头怪脑的事物原来都是远离我的,它们总是发生在那种头脑复杂而且对世界充满了, 199x年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不祥的一年,一些我熟识的和不熟识的年轻人,都在不该死去的年华英年早逝了。我身边就有一位, 陈染:碎音,经典深度好文,优美简短的散文,深度好文章大全,经典短篇散文。
转载请注明:就爱造句网-好句子大全-句子网-在线词语造句词典 » 陈染经典美文,梦回
本站造句/句子文章《陈染经典美文,梦回》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此句子由网友整理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