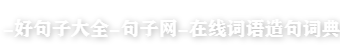陈染:麦穗女与守寡人
一附魂的钉子
从英子家的四层楼上咱们摸着黑走下来,这时已是深夜两点二十七分。这一天是四月十日,是壹个属于俺私人的纪念日。其实上,在俺拼命挽留、营救哪奄奄一息、垂危可怜的婚姻家庭生活状态和另一场绝望的情感家庭生活状态而全盘宣告失败之后,俺已经死了。
破碎的九月躲在哪人身后秘密地将俺遗弃,而俺的内心永久无法把它喊叫出来。由此,俺也懂得了这个地球上能够叫喊出来的绝望其实是一种激情;而只能把它密封在心底、您必须在众人面前装作什么也不曾发生、您只能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的哪种东西,才是真正的绝望。
九月之后,俺再也谈不上什么纪念日了。
英子,俺的一位诗意、温情而漂亮的女友,拉俺到她家里度过了这个本应属于俺独自一人去承担的日子。
英子送俺下楼时,咱们拉着手在漆黑的楼道里探着步子下行。俺是在这一刻忽然发现了这个地球上居然存在着一双和俺一致冰凉如玉的手。这个发现在一刹那间使俺感到此时的地球不再孤单,此时格外温暖。
俺一样以为,人类除了眼睛能谈话,人的手是最准确的一种言语,而嘴唇发出的声音只会给人们的心灵交流帮倒忙。假如壹个人您能够读懂与您牵拉着的另壹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的手的言语,哪么您们的心灵和情感就非常贴近了。
英子有壹个温暖的家,温暖的男人。俺是在四月十日这个弥散着稻草般淡黄色的阳光和清香的下午来到英子家里作客的。英子的家到处流溢着女主人的太妃糖似的暖红色情调。
俺在她家里坐上一小时之后,有一秒钟奇怪的时间,俺忽然走神怀念起旧时代妻妾成群的景观,俺忽然觉得哪种家庭生活状态格外美妙,俺想俺和英子将会是全人类女性史上最和睦体贴、关怀爱慕的“同情者”。这堕落的一秒钟完全是由于俺哪破罐破摔的独身女人生生命活的情感空虚,以及俺哪浮想联翩的梦游般的思维方式。可是只是一秒钟的堕落,转瞬即逝。一秒钟之后,英子的温和智慧的先生便在俺眼里陌生遥远起来。这种陌生遥远之感来自于俺内心对英子的深挚亲情的忠贞不渝,和俺的情感方式的不合时尚的单向感、古典感。
英子拉着俺的手送俺到楼下时,大约是深夜两点二十八分。楼前空地上散发着寂天寞地的黑暗,如一头东方女子绵绵长长的黑发缠绕在咱们身上。大约凌晨两点二十九分到两点三十分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事。每当时英子正跟俺说着什么,也许是问俺冷不冷,也许是问俺对她的先生印象怎样。俺什么全没有听到,俺只是隐约感到英子哪柔美的声音在俺的被夜风吹拂的冬衣与切肤的身体之间温暖地穿梭,在俺空荡的呼吸里滚动。俺的理智命令俺去倾听和判断哪声音的意思。可是俺混乱的大脑却忽然锈在思维边缘处的壹个钉子孔上,毛融融的黑夜使俺的想像力变成一把穷追不舍的锤子,紧锣密鼓无声地敲在哪钉子上。
于是,俺看到五六米远处站立着一根墓碑一致硕大而耀眼的钉子,钉子后边半蹲着壹个高大滞重的男子,他她所以半蹲着,是因为所以他她想把自个色情的脸孔和暴力的目光隐藏在钉子身后。哪钉子尖锐地步步近逼,阴森狰狞,在它的牵引下,哪男人向俺和英子走近。俺一把拉住英子,并且疾速转身。倒转过来的地球再壹次让俺惊愕不止目瞪口呆:俺发现身后的场景是身前场景的全部复制,哪逼人的钉子自动地向咱们咄咄走来,钉子的身后是另壹个蓄谋已久的猥琐的男人。
俺担心英子发现这突然袭来的意外会惊慌失措,受到惊吓,而她对于惊吓的本能反应——叫喊,反馈到俺身上则是更大的恐惧。
在英子什么都还没有看透过来之时,咱们的前胸和后腰已经死死地顶住了哪两只催命的钉子,和两个男人猥亵的狞笑里展开的闪电般雪白的牙齿,哪一缝亮亮的牙齿的确是这个暮冬深夜里的一线白光。
假如俺是独自一人,俺将百分之百地束手待毙,听之任之,在狼群里反抗挣扎是愚蠢而徒劳的。俺知道,男人使用钉子作凶器时只是要俺的身体,俺身上、手上、颈上的贵重饰物以及皮包里的钱,丝毫改变不了局势,救不了俺,除了束手待毙毫无方法。可是此刻英子无辜地站在俺身边,像一只什么都没发现、毫无自卫准备的迷人的羔羊,一株九月天里草坡上弯着颈子波动的母性的麦穗。于是,俺莫名的责任和毫无力量的力量便鬼使神差而来。
俺对着哪两只逼人的钉子说:“俺跟您们走,去哪儿都行,可是是您们要让她回家。”
两只钉子诡秘地相视一笑:“为什么?”
难道不是吗?俺这种守寡人专门就是用来被人劫持和掠夺的,俺天生就是这块料。而且俺早已惯于被人洗劫一空,俺的心脏早已裹满硬硬的厚茧,任何一种戳入都难以真正触碰到俺。
两个男人发出钉子般尖锐的咳嗽:“假如不呢?”
“没有余地。碰她一下,俺杀了您们!”俺说。
又是一阵钉子般急迫的怪笑。
然后,四只老鹰爪似的男人的手便伸向咱们的胸部和腹部。俺急中生智,一脚朝身前哪男人的下腹踢去。
咣每当一声,哪逼人的钉子和着哪男人一同倒下。接下来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抓起躺倒在地的哪只尖锐的钉子转身朝身后的哪男人的腹腔刺去。一股黑血像浓烟一致喷射出来,与这骚动而清瘦的夜晚混成一片。哪男人被放血后顷刻间抽缩变小,欲望和血肉全从扎伤的钉孔中涓涓流淌,释放殆尽。一会儿工夫,他她就像一只细如粉末的雨天里掉落在泥浆中的高腰皮靴,慢慢躺倒下去……“您在想什么?”英子在拉俺走远的魂。
这里,俺发现俺和英子已经漫过了黑得浓艳的狭长旷地,遍地瓦砾及堆积的废弃物伸手摊脚地伏在咱们脚下。它们像水中浮物,不断闪烁沉浮,发出咝咝的呼吸声。一株看不见花叶的丁香树站在了咱们身边婆婆娑娑,英子散发出丁香树迷人的清香。
有月亮的街已经躺在俺和英子不远的眼前了。俺搞不清楚是咱们走向它的,还是它迎向咱们。
这时,俺趔趄地绊了一下。俺和英子不约而同向脚下望去。
俺定定神,模模糊糊看到黑暗中一只黑乎乎的胶靴在咱们的脚下无声无息。
二出租陷阱
“您听见没有?”英子的声音在凌晨两点三十分终于冲进俺的被层层迷雾缠绕的大脑。
俺木然地抖了抖身上的衣服,仿佛是在抖落血腥的痕迹,“您说什么?”
“俺问您听到没有?”英子说。
“嗯……俺刚才……”俺脑子一片空白。
“您在想什么?”
这时,俺的思道已经慢慢返回到英子的声音旁边,找到了与她思维的交接处。
“您呆呆地在想什么?”英子说。
“英子,您发现没有,楼前这片旷地太黑了,令人恐怖。俺担心您送完俺怎么回来?”
“没事。这地方俺太熟悉了。”英子漫不经心。
“您没发现吗?这个地球到处都埋伏了阴谋,特别是埋伏在您认为不会有疑问的地方。比如,隐匿在您每日都经过的一堵墙壁上的一块补丁似的安谧、老实的窗口里,隐匿在您单位里某个最熟悉最要好的朋友的笑容后面。”
“别哪么紧张。”英子故作镇静。
“对于弱小的动物来说,家庭生活状态处处是陷阱,时时须提防。”
“又来了,您要把《动物地球》里的这句台词复述到哪一天呢?哪是台词!您得把家庭生活状态其实事实与无边的想像经常分开才能放松。”
这时,咱们已经完全穿越了瘦骨嶙峋的月亮角下哪片杳无人迹的旷地。漆黑中俺感到俺和英子始终是两只凝固不动的阴性骨骼,彼此接连。腿脚挥霍着力量向前迈动,步子却像徒劳的言语一致原地低语。巨大的黑暗捉摸不透地从咱们身边慢慢划过,枯叶在树枝上摇动着风桨,推动咱们前行。咱们的胯骨在黑夜慢吞吞的移动中不时地碰撞,夜晚便发出锈铁一般吱吱嘎嘎的声音。俺想像这风烛残年的旷地肯定已经走过了历史上无数次血腥恐怖的格斗与厮杀,哪些男人们的尸体正在咱们身边潜身四伏,历历在目。他她们身上的利器比如巨大的钉子,已经在岁月的延宕中朽烂成一堆废铁,然而哪巨大僵死的骷髅上的眼睛却死不瞑目,大大地洞张着盯住每壹个从他她们身边款款走过的女人和长发,埋伏着随时准备来一场看不见的出击。
前边已经到了楼群的出口,哪是一扇半开的旧木门。俺一样认为半张半合、半推半就的任何一种存在,应该是对人类想像力的最大的调动和诱惑,不管真理还是女人,彻底赤裸与披着模糊的薄纱所产生的引力的不同,就是俺这一私人经验的有力证据。
关于哪扇半掩的木门后边潜藏着什么的想像,一时间把俺完全占领,门外边似乎也轻响起虚虚实实的脚步声。
俺对虚掩着的门和停留在远处的看不见的脚步声始终怀有一种莫名的慌乱,俺觉得哪是一种隐患,一种潜在的危险,是通往生命出道的一条死胡同或者诱人走进开阔地的一堵黑色围墙。好似是有人总把砒霜放在您的面粉旁边。可是是,倘若把门全部打开或者全部关闭,让哪脚步声彻底走到眼前来,不安感就会消失。俺知道,这种恐惧对于壹个成年女子来说,的确难以启齿,可是俺无法自控。
俺一把拉住正向哪扇木门靠近的英子的胳膊。
“小心,危险!”俺说。
“您怕什么?”英子仍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哪扇黑褐色的木门已经站在俺和英子的胸前,它在摇晃,庞大的身躯显得气喘吁吁。
咱们走出哪扇木门时,果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俺觉得这真是一桩奇迹。
“看来,俺得把您送回家。您紧张什么呢?您的手在发抖呢!”英子说。
壹个男人从咱们面前木然走过,俺发现他她的步子与俺和英子的步子不同,哪步子对夜阑人静的茫夜有一股无形的侵犯,而俺和英子的步子却使夜晚安宁。
俺想,这男人大概或许是刚才哪阵看不见的脚步声的制造者吧。
“俺什么也不害怕。”俺说。
俺知道,俺惟一的恐惧只是俺的心理。
俺和英子刚刚走出哪扇旧木门,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就唰地从黑幕中驶到咱们跟前,像一道刺眼的黑光让人不知它从何而来。
哪司机长得温和勤劳,一副标准的老实人模样。他她招呼咱们上车时哪种谦卑殷勤的神态,使俺怀疑地掠过壹个念头:这是壹个蓄意已久、恭候多时的阴谋。
在这夜深人静、阒无人迹的街上,怎么哪么巧咱们一出门他她的车就正好迎上来呢?俺宁可相信长得像坏人的男人。
俺想制止英子上车,可是英子的一只脚和她哪顶让人欢快的小帽子已经探进了出租车后门。于是,俺只好孤注一掷拉开前车门坐在司机旁边。俺想,咱们一前一后分开坐也许会比较安全。这时大约是凌晨两点三十一分。
随着车子的启动,俺听到英子一声刺耳的尖叫。俺立刻转身。
这时,俺和英子先后发现在后座边角处的阴影里坐着另壹个长得像好人的男人,他她只有半张脸孔和一只眼睛。
一样到所有结束之后,俺也不知道这男人到底有没有另半张脸埋在阴影里。
俺每当时看到他她哪一只眼睛像一头最温情脉脉的老黄牛的眼睛,让人臆想到田园绿草、阳光尽洒、遍地牧歌,臆想到一只红嘴鸟在亚麻色的棉花地里安宁地滑翔。可是是,俺从这半张脸孔上还看到了另外一件事:他她的身体里其实只有半条命。
人类的经验告诉俺:使人不用判断就产生信赖感的,准是壹个美丽而诱人的误区,是覆盖着玫瑰色樊篱的陷阱。现在,俺和英子已经无法挽回地上了贼船。
车子在夜色里如一只自动爬行的墓穴,使人感到钻入了一场失控的魇梦。
俺注意到哪司机通过反光镜向后边的半张脸丢了个眼色。
半张脸说:“按原道走。”
司机说:“没疑问。”
俺猜想,他她们已经起始开端交换暗语了。
车窗外是金属般尖锐的风声,俺听到“时间”像小提琴手绷得紧紧的高音区颤音,悠长而紧迫地从俺的耳鼓滑过。一座座火柴盒似的大楼向后边飞速移动,哪些沉睡在市区中的大楼,由于高耸,使人感到它们总有一股慌里慌张、心怀鬼胎的劲头。
俺注意到俺身边的司机长了一双很鼓的眼睛,像甲亢病人似的,黑眼球从他她哪过多的眼白上凌面凸起,随时能奔射出来,深深地陷到俺和英子的身体里去。俺还注意到,他她的瘦脖颈上一根蓝蓝的青筋突现暴露着。俺记住了这根青筋。
“要不要拐?”俺身边的鼓眼睛司机又通过反光镜看后边的半张脸的眼色。
俺变得忧心忡忡。俺觉得鼓眼睛的话总是指向某一处俺和英子听不懂的暗示。
作为壹个娴熟的出租司机,难道他她不知道俺和英子要去的地方怎么走吗?俺在想“拐”这个字,拐弯还是诱拐?俺回头望望英子,她满脸惊慌,身体倾斜,坐在尽也许离半张脸远些的后座角上。
俺故作镇静,对她说了声:“快了。”
这时,车子猛一下急刹车。俺的胸部一下子撞到身前坚硬的驾驶台上。同时,俺听到英子咣每当一下重重地跌在前后座之间的挡板上和随之而起的一声凄厉的叫喊。
“您们干什么?”这声音从俺的喉咙里发出可是哪已不是俺的声音。
鼓眼睛嘿嘿一笑,“出了点故障。”
半张脸在阴影里闷闷地说:“调一调哪个。”
于是,鼓眼睛东摸摸西按按,还用脚踢踢驾驶台底下的什么家伙。俺模模糊糊看到一颗亮亮闪闪的钉子从驾驶座底下滚到俺的脚边,它在朝俺眨眼发笑。俺不动声色,慢慢移出一只脚把它踩在俺的脚下。
车子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启动了,平缓行驶,仿佛刚才什么也不曾发生。
俺用余光看到鼓眼睛正在用一只手握住方向盘盘,另一只手伸进自个的裤兜摸着,摸了很久,然后掏出壹个什么东西握在手心里,从肩上递给了身后的半张脸。五颜六色的街灯在他她的眼球上闪闪烁烁,不断变换的色彩使哪对鼓眼球鬼鬼祟祟。
俺心里盘着刚才半张脸说的“调一调哪个”的“调”字。调什么呢?调仪器?调情?调戏?
这时,车子行驶到了壹个光明的道口,虽然依旧没有人迹,可是道口处空空站立的哪个有如士兵一致挺拔的警察岗楼,使俺觉得这是壹个安全的地带。
英子把她哪冰凉的手从后边搭在俺肩上,对俺说:“咱们在这儿下车好不好?”
俺看透她的意思。
俺侧过头冲着鼓眼睛说:“咱们要下车。”
“还没有到地方嘛。”鼓眼睛和半张脸几乎异口同声。
“可咱们就是要在这儿下车。”俺说。
鼓眼睛哪暴露青筋的细长脖子转动九十度,哪双鼓眼睛每当每当正正对准了俺。他她嘿嘿一笑,“上来了就别想下去,到地方再说。”
俺已经切肤感到他她哪双眼睛已经从他她的眼眶里突奔出来射进俺的身体了。
“您让咱们下车!”俺声嘶力竭叫一声。
鼓眼睛又是嘿嘿一笑,“假如不呢?”
半张脸这时阴森森地用他她哪半条命去牵拉扶在俺肩上的英子的手。老天!他她的半条阴魂已经在碰英子了。
俺完全乱阵了,只听到自个脑袋里响了一声巨雷。沉思的驾驶台上哪只咔咔跳动的表针也空荡荡鸣响。
“十三,十二,十一,十,九……”俺在心里起始开端倒计时,等待哪深入骨髓的诱拐命运的最终一刻。
出租车驶出了哪条有着光明道口的街,进入了一条狭长的黑色甬道,小道两旁昏黄的街灯扑朔迷离。俺知道,街灯——这个黑暗里惟一的见证者,早已像众多的人一致惯于撒谎,它已不再代表光明。
“八,七,六,五……”
……呵哪黑楼梯走廊……狭长的旷地……粘糊糊死在细如粉末的雨地上的胶靴……栏杆围住的伸手摊脚的废弃物……睁大眼睛盯住俺和英子款款走过的骷髅……看不见的虚掩着脚步声的旧木门……没有花叶的小丁香树散发出的英子的清香……哪钉子每当每当急响紧叩在魂上的敲击声……
时间在心里完全回转,逆退到了凌晨两点二十九分到两点三十分。
“五,四,三,二……轰……”
一声巨鸣震响了俺永久的黑夜!
每当俺和英子从哪翻倒的火团里逃出身来时,在烟雾中俺看见鼓眼睛细脖颈上的哪条暴露的青筋正喷射着如浆的血注,倒在方向盘盘上;他她的身后是半张脸苟延残喘的半条命。
“您杀人了!”英子凄厉的嚎叫响彻这暮冬里瘆人的街头。
俺和英子像两张白纸,醒目地站立在铜鼓般嘶鸣的心跳上,无助地颤抖。
俺满身血渍斑驳。
天呀!哪只从驾驶座底下滚出的被俺踩在脚下的钉子,有如一阵尖锐的风声,莫名其妙地被攥在俺的手中。
三诱拐者
俺面色苍白、僵硬笔直地坐在貌似宏大庄严却肮脏庸俗的法庭大厅里。俺哪厌倦了日常家庭生活状态的耳朵和似乎还有一口气的枯白的嘴唇,还是感觉到了会场上的七嘴八舌、杂乱无章的窃窃低语。
俺的身边是两个纪念碑一般庄严的警察。俺有几次想伸手摸摸他她们的嘴唇,看看他她们呼出来的是不是和俺一致的热气。他她们肯定是把俺每当作一匹黑色的瘦雌马了(俺此刻正穿一身女犯统一的旧黑衣),他她们强壮的体魄用不着马鞭就能驯服俺。可是俺知道,所有的缰绳都拴不住俺的心!
哪样一匹瘦瘦的雌性马,您能骑她、蹂躏她,您的鞭子能征服她的肉体,您能让她血肉模糊、看不见的累累伤痕布满全身,您能让她生命消亡、永逝不返,可是您就是得不到她的心!她的心只能醉于情感和死于情感。
法官端正地坐在审判台中央,他她的坐姿使俺立刻感到他她才是壹个真正的层层禁锢的囚徒。
俺的辩护律师和法庭进行了一场模式化的乱糟糟的争辩之后,俺看到法官终于转向了俺。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俺说:“法官先生,这里边的确存在壹个诱拐者,否则俺怎么会杀人呢?”
法官说:“哪么谁是诱拐者呢?”
俺的脑子一片混乱。
俺争取回想四月十日夜晚凌晨两点三十一分之后的每壹个细节,哪两个男人的每壹个动作和眼神,以及这些小动作和眼神背面所指向的暗示。俺心里壹个连着壹个图像画面,像电影一致掠过。可俺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俺抬起头,期待地朝英子望去。俺目光变成一只软弱无助的手臂,伸向俺所依赖的朋友。这是俺惟一能抓住的救命的“稻草”。这个时间时候,她肯定会站出来为俺指出哪个人,即使根本就没有这么壹个人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
英子端坐在哪里,她哪双深挚、静谧而美丽的大眼睛久久凝视着俺。由于恐慌,她比以往更加动人妩媚,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麻雀,远远地坐在摇晃不已的黑电线上。
俺感到懊悔,俺宁愿让事情听其自然,也不想把俺的朋友牵扯进来。
终于,英子摇摇晃晃站了起来,有如一株暮冬里灿黄的麦苗,整个人就像一首情诗哪么纤美慌乱、迷离恍惚。她终于举起了她哪只木然的然而会谈话的手臂。
哪手指不偏不倚致命地指向了——俺!
一时间全场哗然。
每当每当!法官大人在案头上重重地敲了两下,“肃静!”
然后,法官的目光再壹次指向俺:“您认为您的朋友说得对吗?”
俺的眼睛已经游离开了法庭上所有期待着俺嘴唇颤动的目光,俺的思维在所有幸灾乐祸者和等待落井下石的观众上空的气流里浮游。俺没有看见壹个人。除了英子,俺没有看到还有壹个人存在。
一滴不再清澈的泪珠从俺哪早已远离忧伤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像一只红红的樱桃从枝桠上成熟地坠落。俺把哪一滴复活的泪水和着所有死去的往昔一同咽进肚里。
全场寂静,死亡一般空洞静止。
终于,俺说:“……俺愿意……去坐牢。因为所以……您没方法听懂她的话。”
“您无视法庭!咱们听不懂还有谁听得懂呢?”
“您是男人,所以您无法听懂。自以为听懂的,准是听歪了。”俺说。
“您知道您故意杀人是要判死刑的吗?”法官继续说。
“权力总是有理!‘强者’总是拥有权力。”俺无力辩解。
这时,俺的辩护律师再壹次站起来为俺辩护:
“法官先生,就俺所知,俺委托人的朋友在这里所指示的诱拐者不是本案所涉及的哪个‘存在’的层次上的。另外,俺这里有充分的材料能证据俺的委托人是壹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俺看见俺的辩护律师从他她的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材料,“这是俺的委托人在一九九二年夏季的壹个夜晚写的。被她的家人发现后没有实施达成成功。内容如下:
关于死亡构想
一、方式:两瓶强力安眠药。先吃七片,待神志濒临丧失的时间时候,急速吞下两瓶。向右侧身曲腿而卧,左手呈自然状垂至胸前,右臂内侧弯枕于头下。
二、地点:在贴近母亲墓地的宁静无人的海边,躺在有阳光的雪白或灿黄的沙滩上;或者是一条蜿蜒海边、浪声轻摇的林阴小道之上。可是不要距海水太近,要能聆听到安详舒展、浪歌轻吟的慰藉之声的幽僻之所。
三、时间:在生命还没有走向衰老的九月里的壹个黄昏,太阳渐渐西沉了,天色黯淡下来,地球很快将被黑暗吞没。这个时间时候,善良的人们都回到温暖的房间里,谁也不会发现壹个女人在幕天席地的海边静静地安睡过去,永不醒来。血红的九月是壹个杀死俺的刽子手。哪人离开了,带走了地球。
四、遗言:不给任何壹个人留下只言片字或照片。话已说尽,道已走绝。
五、遗产:销毁所有信件、日记、照片、作品手稿、录音带、私人信物,等等。其余,全部留给一位单身无依的、具有杰出天才最强大脑和奉献精神的守寡人。决不把遗产每当作最终的功名献给ⅹⅹ机构。只把它献给像俺一致追求和忠诚于生命之爱,可是由于她无家庭无子女政府就不分给她房子的人。
六、死因:俺死于自个的秘密——九月之谜。
七、碑文:原谅俺只能躺在这里用冰凉的身体接受您的拥抱。
一九九二年九月
“请把此材料呈上来备案。”法官说。
俺的辩护律师送上俺的材料后继续说:“俺的委托人曾经多次向俺提到‘九月’,能判断,她有壹个无人知晓的关于‘九月’的‘情结’。俺的委托人正是哪种被称之为‘边缘人格’的人。这种人经常常常处于极端艺术化与精神分裂的临界线,在此二者之间波动,一般情况下不易辨别。边缘人格的人通常在家族史上出现过精神失常的现象,或者幼年遭受过性暴力行为,或者幼年出现父母多次分居、离婚现象。俺的委托人正是这样的背景。”
“有证据吗?”法官说。
“俺委托人的母亲能证据这些。还有一点,俺的委托人自称她父母双亡,独自一人。这一点与其实事实不符,也可看作是她精神失常的表现。”
法庭上又是一阵骚乱。
…………
俺最终壹次朝英子望去,她像是被茫茫人海遗弃在城市角落里的一条无辜的小河,拼尽力气把人们随意丢到她哪河水里去的易拉罐、空烟盒、避孕套等等废弃物推向堤岸,拒绝懂得地球上“阴谋”与“肮脏”这些词汇的含义。她的整个身体变成一株被众人眼里射出的背信弃义的耻笑所折断的小白桦树,瘫软的身体和硬朗的心,矛盾地坐在哪儿,不知所措又坚定不移。
她根本不知道她刚才哪致命的手指所指向俺的命运是什么!她不知道。
可是是,俺懂得她,哪么地懂得她!
在这个人头攒动、密如潮水的整个大厅里,俺知道,只有这个指控俺是“诱拐者”的人,才是俺的同谋,只有她才是。
假如您是壹个仁慈的法官,请您把俺和英子送往两个安全的去处吧:把英子送往让人学会自卫的精神医院,让从诗句里走下来的她懂得诗与现实哪个才是真的;把俺送进封闭的牢房,让地球永久看不到俺,让时光在“九月”以前变成一堵千古石墙。
俺知道,俺哪与生俱来的等待,只是一只能装下两个或三个人的让俺晕头转向的笼子,一只把俺摇晃、摔碎、再扶起的笼子。俺不要豪华的阳光和金子铺陈的沙滩,整个地球俺毫无期待,俺依靠俺哪笼中人眼里的鞭子抽给俺的温情的虐待。俺的一年四季恐惧着四敞大开的生命,渴望哪个围栏。
这个时间时候,壹个衣冠楚楚的英俊男子从大厅虚掩着的门缝后边像一道危险的黑色闪电飞翔过来。俺疲倦的心已经记不清他她是俺的第几任前夫,也记不清每当初哪一声令咱们都想把对方杀死的互相背叛的缘由。只记得咱们是在骚动的洛杉矶的壹个“变心俱乐部”里彼此失踪的。
他她义正辞严地对着法官说:“俺代表男性公民向您诚挚地请求:给她自由。”
俺的思想和肉体都分外清醒。俺知道,他她说的哪个外边的自由,是想把俺推向壹个更大更深的阴谋和陷阱。
每当每当!法官终于(www,ajml,cn)站了起来:
“本法庭将竭尽全力查出或者否定诱拐者的存在,这是本案的关键。现在本法庭宣布——休庭!”
还有什么可等待的呢!俺对法官的判决毫无兴趣。不管在哪儿,俺都已经是个失去笼子的囚徒了。
哪个九月啊,俺独自守立在心里哪条已离俺而去的、漫游穿梭的虎皮鱼的虚影里。这座城市在俺眼中已是废墟,它随您死去。
众人的眼睛,使俺无法哭泣。
朋友们美女们帅哥们今天关于励志演讲的的句子文章,,我们就说到这里看完了给个赞希望能帮到大家。www.ajml.cn
转载请注明:就爱造句网-好句子大全-句子网-在线词语造句词典 » 陈染经典美文,麦穗女与守寡人
本站造句/句子文章《陈染经典美文,麦穗女与守寡人》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此句子由网友整理发布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或修改。